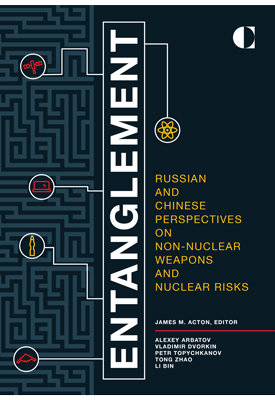
核交缠:中国和俄罗斯对无核武器及核风险的看法
交缠引起的升级风险有多严重?中俄两国作者的观点与其所在国家战略界的观点有何不同?
概要
非核武器与核武器及其支持力量的交缠正在加剧意外升级的风险。但迄今为止,参与该意外升级风险严重性的讨论几乎仅限于美方。鉴于此,卡内基的俄罗斯和中方专家也着手研究此问题,并致力于解答两个疑问:交缠引起的升级风险有多严重?作者的观点与其所在国家战略界的观点有何不同?
交缠的定义
交缠有多重体现,包括核弹头和非核弹头通用运载系统;核力量和非核力量及其支持架构的交错;以及非核武器对核武器及其指挥、控制、通信和信息(C3I)系统构成的威胁。目前,技术的发展使得非核武器与核武器及其支持力量的交缠日益增加。
阿列克谢·阿尔巴托夫(Alexey Arbatov)、弗拉基米尔·德沃尔金(Vladimir Dvorkin)和彼得·托皮契卡诺夫(Petr Topychkanov)的俄罗斯观点
美俄科技和政策的发展推动形成了交缠的局面,即使局部的非核冲突也可能在无意间迅速升级成为全球核战争。然而,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政客和军事专家都根深蒂固地认为升级核战争一定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不会经由意外发生,因此没有恰当地对意外升级危险进行评估。
俄罗斯政策与交缠
“空天战争”是俄罗斯当代战略思想的核心,但其定义并不明确。俄罗斯战略家设想的似乎是相对持久的冲突,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组织,NATO)对俄罗斯发起非核空袭和导弹攻击。由于俄罗斯抵抗攻击的能力有限,因此它可能不得不借助核武器迫使美国及其盟国撤退。这样的冲突涉及核作战和非核作战、防御能力和进攻能力、弹道武器和飞航武器,而这样的情形下必定发生交缠。
非核战略武器的影响
由非核高精度武器引发的大规模解除武装打击的威胁一直以来都是俄罗斯领导人的心腹大患。美国如果在非核冲突中发起袭击,可能会在无意中引发俄罗斯方面对美国是否会开展解除武装打击的担忧。比如,原本针对常规海军舰艇和飞机展开的打击,也可能无意中摧毁同一基地的战略潜艇和轰炸机。
即便如此,假如美国在导弹防御支持下,尝试用常规巡航导弹——以及将来研发的高超音速助推滑翔武器——展开解除武装打击,能取得怎样的效果也非常令人怀疑。事实上,俄罗斯已经投入资金发展这种能力建设,为其核力量的生存保驾护航。
这或许会让俄罗斯领导人的担忧显得不那么必要,但其担忧实则源于对大规模核反击威胁能否阻止敌人以常规武器进行先发制人打击的疑虑。不过,俄罗斯政府实际可能会采用范围有限的战略核打击,甚至可能在发现美国海军和空军准备或已经发起大规模空天袭击时,率先选用战略核武器粉碎美方计划。
俄罗斯核力量和常规军事力量共用军事基地的现象早在苏联时期就已存在,一直是出于经济和行政方面的考虑,并非试图通过核升级危险,以阻止美国对俄常规军事力量展开非核打击。
现在,俄对美战略基地发起非核打击的能力还十分有限,但其可以通过购买高超音速武器加强该能力建设。不过,选择性打击不列颠、格陵兰、阿拉斯加等地的雷达既可以干扰导弹袭击预警,又能破坏弹道导弹防御作战,此举可能带来常规战争升级为核战的风险。
反太空武器与交缠
美俄两国似乎都有非专用但潜在的强大反卫星能力。据俄方人士介绍,北约组织的高级高精度远程非核武器需要依赖太空系统的支持,如此明显的弱点,俄罗斯即便在非核战争中也不可能忽略。当然,俄罗斯也担心自己的卫星受到威胁。
非核冲突所打击的卫星可能同时也服务于美国或俄国的战略核系统,这也会引发交缠。由于战略力量很可能属于最高警戒状态,所以即使在局部武装冲突中摧毁战略核系统预警卫星,也可能会立即升级为核战争。
通信卫星也可能成为打击目标,因为部分卫星对海上导弹艇和巡逻轰炸机的指挥控制非常重要。而袭击预警卫星则更加危险。虽然非核战争的反卫星作战不太可能影响到预警卫星,但很难对此做出保证。特别是对于必须冲破对方导弹防御的选择性核战略打击或常规战略打击而言,可能首要做法就是让对方的预警卫星失效。
而俄罗斯的预警卫星一旦失效,便可以视作反击前兆,促使俄政府启动洲际弹道导弹(ICBM)发射行动,不过根据标准程序,实际发射可能需等候地面预警雷达给予攻击确认或确信这些雷达已被毁坏。
赵通和李彬的中国观点
交缠引起的意外升级风险真实存在并且与日俱增。但由于中国的政策选择,实际风险没有很多外国专家认为的那般严重。
中国关于升级的战略思想
意外升级一直不是中国传统军事思想所考虑的要素。此外,中国基本没有直接经历过严重核危机,这与深受其害的苏联和美国不同。
近年来,中国开始逐渐重视意外升级,但由于体制内部的分化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进展受阻。大部分(若非全部)中国专家坚信中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并认为此承诺对于避免升级有很大帮助。很多专家都认为,军事技术本身不会改变升级的可能性,反而是具体的军事技术部署和使用策略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另外,中国专家怀疑,美国之所以强调升级风险,其实意在破坏中国正当的军事现代化工作。
多功能与模糊性
冲突期间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某些武器和军事装备,可能因其多种用途而引起意外升级。比如,有中国专家指出,常规战争期间,中国会考虑摧毁美国的预警卫星,确保中国常规导弹可以有效打击区域性目标。美国则可能认为中方此举具有特别的挑衅性,旨在蓄意破坏美国的战略防御能力,使之无法拦截中国向美国本土发射的洲际弹道导弹。
部署或使用可以同时威胁核目标和常规目标的进攻性武器,同样会引起误解。比如,有些水下无人潜航器可以同时威胁敌人的弹道导弹核潜艇和攻击型潜艇。即使美国只想威胁中国的攻击型潜艇而非弹道导弹核潜艇,中国仍有可能怀疑其海上核威慑能力面临危险,这样的风险确实存在。
中国不是为了保护非核力量而将核力量与非核力量交缠部署。但在中方发现核力量与非核力量的交缠可能有助于对其非核力量的保护的情况下,中国可能没有特别的意愿对二者进行分离部署。
关于武器部署和使用的不同观点
对部署特定武器的目的和影响或武器使用倾向的不同观点可能引起误解。比如,美国可能会高估中国在冲突期间使用反卫星武器的可能性,一旦发现中方可能采取此类行动的模糊迹象,便容易反应过度,对中国反卫星资产和设施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
同时,美国称部署到韩国的末段高空区域防御系统(萨德,THAAD),只在于防御朝鲜导弹。但中国专家却得出美国其实意在中国的结论,并称中国应当在中美军事冲突时做好攻击萨德系统的准备。如果中方真的打击萨德系统,那么中美双方会对中国的意图产生截然不同的理解。中国会认为自己的打击行为完全可以理解而且十分正当,不应当激起美国的过度反应。反之,美国决策者则可能解读出极度挑衅的意味。
交缠与风险承担
某些非核技术的开发和部署可能影响一国在危机期间承担风险的倾向性,从而增加或减少危机升级的可能性。例如,中国专家根据美国官员和媒体报道的说法,认为美国政府正探索使用网络武器,在发生危机时破坏潜在敌人的战略导弹和核C3I系统。美国要想开发这种网络能力,需要在和平时期对敌人的网络基础设施进行不断的渗透和探测,以发现潜在漏洞。敌人可能偶尔发现美方的网络探测行动,从而担心其核威慑体系可能受到网络攻击。危机期间,高度的漏洞意识可能让国家更加不愿承担风险,从而倾向于在冲突早期使用核武器。
加重战争迷雾
某些非核技术的引进可能减弱、也可能加重战争迷雾,从而影响意外核升级风险。有的中国分析人士,尤其是赞同在中美局部战争中使用反卫星武器的分析人士,往往将由该打击导致的战争迷雾看作是中国的战术军事优势。但这带来的另一个后果是,美国可能将中国军演、调动导弹部队等军事演练行动误解为中国准备使用核武器,因而可能对中国核力量或设施启动先发制人的打击。战争迷雾也会阻碍一方与敌方之间有效的信息沟通。美国不断加强使用无人水下潜航器等可能破坏中国核能力的无人军事系统,增加了这方面的风险。
詹姆斯·阿克顿(James Acton)提供的美国对政策影响的看法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越是认为意外升级不可能发生,反而越会增加此类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持有此种观点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在和平时期不太会采取措施降低风险,在战争时期却会按最糟糕的情况来解读模糊事件。虽然没有太多证据表明美国对此已给与了足够重视,美国政府仍应优先考虑降低此类风险。
单边措施
由于中美、美俄政治关系恶劣,且关于哪个国家是造成升级风险的罪魁祸首说法不一,现在单边措施是降低风险最实际的方法。危机期间加强战略决策者对意外升级风险的意识、并在制定政策和规划战争时考虑到此风险,会有很大助益。理想情况下,中美俄三国都应当依此行事,无论其他两国有何举动。
政府间对话
中美、美俄政府间对话的开展更具难度。政府间对话最初的主要目的很简单:深入了解潜在敌人的观点,更准确地评估升级风险。先进常规武器、太空核C3I资产的生存能力以及网络武器与核C3I系统的相互作用都可以是讨论的初步话题。
合作措施
长期看来,建立信任措施甚至正式控制军备对于降低风险都有重要作用,不过眼下此类操作前景黯淡。尽管如此,政府可以也应当启动制定和评估提案的工作。美国和俄罗斯应当评估制定透明度协议,阻止向对方“战略目标”范围发射巡航导弹的空射和潜艇平台“秘密集结”,协商禁止测试、部署专用反卫星武器,同时洲际助推滑翔系统不得超过《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后续条约规定的限度。
多边合作面临重重挑战,但无论美俄、美中存在怎样严重的分歧,没有哪个国家希望其降低意外升级风险的努力在出现了严重的核战争风险之后才起作用。
近几年来,由于非核武器与核武器及其支持力量的交缠,意外升级风险的严重性再次引发讨论。这类交缠有多重体现,包括核弹头和非核弹头通用运载系统;核力量和非核力量及其支持架构的交错;最重要的是,非核武器会对核武器及其指挥、控制、通信和信息系统构成的威胁。
迄今为止,这一讨论至少在两个重要方面受到限制:一是参与讨论的几乎只有美国,二是讨论的焦点几乎完全集中于中美冲突。然而,交缠没有明显理由不会引发美俄冲突升级(事实上,第一次严肃考虑交缠的后果恰恰是在20世纪80年代美苏冲突背景下发生的)。此外,考虑到各方看法对于推动事态升级有相当的重要性,如今中俄两方的观点缺失无疑成为一个严重问题。
本书尝试补充中俄两方观点。主要作者均为中俄两国杰出且著名的核政策学者:Alexey Arbatov、Vladimir Dvorkin少将(已退休)、Petr Topychkanov、赵通和李彬。他们致力于解答两个问题:交缠引起的升级风险有多严重?作者的观点与其所在国家战略界的观点有何不同?我在结论部分针对各位作者回答的政策影响阐述了自己的看法。
感谢纽约卡内基基金会,如果没有该基金会的大力支持,本书无法完成,同时,感谢参与中俄研究团队工作的诸位现任和前任政府官员、军官、国防工业代表及非政府分析人士。由于所有访谈均以匿名形式进行,我们在此不能向受访者和研讨会参与者逐一致谢,谨在此向他们表达感激之情。
詹姆斯•阿克顿
华盛顿特区
2017年7月
关于作者

联席主任, 核政策项目
詹姆斯•阿克顿(James M. Acton)主要研究核威慑、裁军、不扩散以及核能等问题。
- 采取综合之策,重新构想核军备控制报告
- 交缠导致升级:指挥控制系统的脆弱性将如何增加非故意核战争的风险媒体报道
阿克顿 詹姆斯•
最新作品
交缠是由一些新型非核技术的发展所导致的,这些技术可对核武器及与之相关的指挥、控制、通信和信息(C3I)系统构成威胁。交缠正在逐渐增加风险,很可能会导致大国之间的非核冲突(即使只是局部冲突)迅速升级并意外发展成全球核战争。出于对战争性质根深蒂固的观念,即,战争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是通过其他手段开展政治活动的延续”,各国(包括俄罗斯)的政治家和军事专家都低估了这种危险。[1] 这是摘自普鲁士将军、军事战略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的言论。这种理念催生了当代俄罗斯战略家的一种本能的假设,即使用武力(包括核武器)的决定将是合理的举措。
曾有一项推论指出,由于大国(俄罗斯、美国和中国)将在核战争中不可避免地遭受毁灭性打击,因此,它们都不会主动发起这种战争,这也令这一类冲突爆发的可能性变得微乎其微。这一推论是以明确无误的相互核威慑理论为依据的,而相关的评估结果,即,无论是美国还是俄罗斯都无法将报复行为所带来的损害降低到可接受的水平(无论是何种水平),则再次肯定了上述说法的正确性。俄罗斯的军事和政治思想基本上排除了“意外引发战争(即,因一系列军事反击行动不受控制的升级而导致战争的结果)”的可能性。[2] 新一届的美国政府也对此表示赞同。
但战争史(尤其是自1945年至今的历史)却再一次证明,大国之间的战争很可能是因两国的一系列军事反击行动所引发的危机或涉及盟国的局部战争的升级而导致的,而不是由有计划的大规模侵略行动而导致的。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牵涉进攻行动,双方也都倾向于认为自身的行为纯属防御性质,同时也倾向于认为敌方发动了具有侵略性的行为或作出了不恰当的反应。
在冷战时期,超级大国总是设法在爆发直接冲突前悬崖勒马。
1962年10月的古巴导弹危机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在这场危机中,尽管双方都不想发动战争,并且对爆发战争的可能性都心存忌惮,但最终避免全球核灾难纯属老天庇佑。虽然这场危机很可能是冷战中最危机四伏的事件之一,但它绝不是唯一的。其他的危机和冲突(包括1956年至1957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1961年的柏林危机、1967年和1973年阿拉伯与以色列之间的中东战争)都曾濒临失控。在上述每一次事件中都存在爆发核战争的特定风险,因为前苏联和美国都(在不同程度上)涉身其中。
在冷战时期,超级大国总是设法在爆发直接冲突前悬崖勒马。尽管从“向对方发动毁灭性打击”这个层面上来说,俄罗斯与美国之间的核威慑仍然维持了稳定的态势,但在当代日趋复杂的世界秩序中,我们总有一天会耗光这种好运气,并将承担可怕的后果。
两种趋势令这种风险日趋恶化。第一个趋势就是国际关系的普遍恶化,包括在叙利亚和乌克兰以及俄罗斯与美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之间日趋紧张的军事对峙。这一对峙态势涵盖广阔的区域(包括地中海、黑海、波罗的海和北极地区)。在西太平洋地区,中国与美国及其盟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也日益白热化,不过,这一紧张局势目前不如欧洲严峻。
第二个趋势就是全新的军事技术和新兴战略概念的发展(例如“核降级”和“有限的战略核交锋”)。其中特别重要的就是全新非核武器的开发,这些武器可以用于攻击敌方的核武器、部署这些核武器的基地以及与之相关的指挥、控制、通信和信息系统。这种交缠破坏了核武器和非核武器之间以及进攻和防御系统之间的传统界线,同时还可能令大国间的局部常规武装冲突以迅速且令人意外的方式升级为核战争。
在冷战结束后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内,这种军事和政治因素的结合出人意料地将大国之间的武装冲突(甚至是核战争)威胁再次推向了国际安全议程的最前线。最令人担忧的是,目前仍无法确定:俄罗斯和美国的当代政治和军事领导人是否已经认清了这种危险(例如在叙利亚、乌克兰或波罗的海地区的危险)。
本章从俄罗斯的观点入手,阐述了因交缠而产生的风险。具体内容可以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我们探讨了俄罗斯国内相对较新的理念,即,关于涉及“空天武器”的大规模战争的概念。这一概念正逐渐成为俄罗斯国防战略的核心,并很可能会令与交缠有关的战争升级风险进一步加剧。第二部分侧重于探讨俄罗斯对“美国利用高精度常规武器对俄罗斯核部队以及指挥、控制、通信和信息系统进行动能打击”以及“俄罗斯针对美国发起类似打击行动”的立场。第三部分讨论了俄罗斯对美国卫星构成威胁的能力及相关的理论,具体包括其指挥、控制、通信和信息系统的关键要素以及俄罗斯对“美国打击俄罗斯太空资产的类似能力”的看法。贯穿所有分析内容的一个共同点就是:俄罗斯全新的空天部队的作用。俄罗斯武装部队的这一全新单位于2015年8月1日由俄罗斯空天防卫部队和俄罗斯空军合并而成,它主要负责防御空天攻击并组织空袭和太空进攻行动。[3]
本文并未详细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对核武器及其指挥、控制、通信和信息系统的网络威胁。鉴于这些问题具有高度保密性,即使只是涉及网络武器对核风险升级可能产生的影响等问题,我们也无法妄加评判。此外,由于战略核部队的指挥和控制系统是完全独立且受到严密保护的,因此,它们遭遇网络攻击的可能性很可能微乎其微。用于控制卫星并与之进行通信的无线电波道(尤其是导弹预警设备的无线电信道)更易于受到攻击。破坏这些波道或利用其创建导弹来袭的虚假信息很可能会引发意外的核战争,尤其是在美国和俄罗斯都确定了在发出攻击警报时就发射洲际弹道导弹(ICBM)的计划和系统的情况下。(如果未来部署高精度的远程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的话,这种风险很有可能会进一步恶化,因为陆基雷达无法及时确认涉及这种武器的攻击是否已迫在眉睫,这就意味着,只有在接收到卫星发来的警报后才能发射洲际弹道导弹。)由于网络干扰指挥、控制、通信和信息系统的后果很可能涉及意外的核交锋,因此,世界上的任何大国都不太可能采取这一类行动。在危机局势中,恐怖分子或流氓国家更可能成为这一类行动的发起者。大国之间可以通过合作制定出一套规则和程序来侦查并交换关于网络攻击的信息并共同确定其来源,从而降低这种风险。
空天战争
“空天战争”是俄罗斯的安全话题中被广泛讨论的最重要概念之一,但它同时也是该国当代的战略思想中定义最模糊的一个课题。俄罗斯目前盛行的军事理论认为,军队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为俄罗斯武装部队的最高指挥官及时”提供“关于空天攻击的警报”,同时“保证俄罗斯联邦的关键要塞有能力抵御空天攻击并[确保]其维持可击退空天攻击的战备状态”。[4] 不过,这一理论并未针对空天攻击作出明确的定义。
同样,经常讨论空天战争理论的专业军事报告也并未对空天战争的目标和手段作出清晰准确的定义。不过,这种缺失并没有阻碍对这一概念的广泛探讨。其中的一个例子如下:
对全球军事和政治局势发展态势的分析表明,就目前和近期来看,对俄罗斯联邦战略要地的潜在攻击威胁就是空天攻击。事实上,空天战场对俄罗斯的威胁程度只会日趋恶化……空天领域本身将成为主要(有时甚至是唯一)的武装冲突领域,其中的军事行动将在全球范围内发挥关键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敌方将有机会从时间和空间维度对俄罗斯领土内(乃至整个世界范围内)的几乎所有目标发动协调一致的高精度打击行动。[5] (重点标识为作者所加。)
在这一背景下,俄罗斯军事和技术专家目前正致力于拟订赢得空天战争的详细战略。我们试图在下文中阐明来自军事俄罗斯空天防御军事学院的知名理论家尤里·克里尼特斯基(Yuri Krinitsky)上校所制定的这一类一体化理论框架:“空基和天基攻击手段的一体化趋势已将空域和太空转化为武装冲突的特定领域之一:军事行动的空天战场。针对[美国]空天部队在这一战区内联合一体、井然有序的武装行动,俄罗斯空天防卫部队应以同类行动予以反击。这样才能符合《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战略》和俄罗斯总统于2006年批准的《空天防御计划》的要求。”[6] 该文件还列举了空天防卫部队的任务列表,包括“监测并侦察空天领域内的情况;识别飞机、导弹或太空攻击的苗头;向俄罗斯联邦的国家机关以及相关的军事领导人提供与之有关的信息;反击空天攻击行动;以及保卫俄罗斯的高级指挥所和军事指挥部门、战略核部队各单位和导弹警报系统的各个作战小组”。[7]
虽然对空天防卫部队(目前已成为空天部队的一部分)[8]的组织、操作和空中技术问题大肆抨击,但军事分析人士却回避了关于何为“空天攻击手段”(在俄语和英语中分别简称为SVKN和MASA)的基本问题。这一术语和“空天攻击”广泛应用于官方文件(包括军事理论)和声明以及军事组织(例如:空天部队)的新名称之中,不计其数的专业报告、书籍和宣传手册也援引了上述术语。
如果空天攻击手段指的是飞机和巡航导弹,那么“航天”一词又与其有何关系呢?可以肯定的是,各种军事通信和情报系统以及侦察和监视卫星都是以太空为基础的,但这些资产同时也为海军和陆军部队所用,但它们的名称中并不包含“太空”一词。
如果空天攻击手段指的是绝大部分运动轨迹都位于太空之内的远程弹道导弹,那么这一威胁就称不上新鲜事物了,因为它们早在60多年前就已经面世了。尽管美国和俄罗斯在导弹防御方面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无论是过去、目前、还是未来,两国都不具备可抵御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的防御系统。在过去(目前或许也如此),弹道导弹的一项可能的任务就是摧毁敌方防空系统中的“长廊”,并帮助轰炸机成功突防。不过,随着弹道导弹装备的弹头日渐增多且精度日趋提高,加之远程空射型巡航导弹的出现,对轰炸机突破敌方防空系统的需求已经日益减少。空中与概念上的“太空”系统之间的协调合作显然已转移到了战略规划的背景之下。不管怎样,这种战术以前从未被视为空天战场。
空天攻击手段的用途可以参考潜在的高超音速助推滑翔武器的情况,我们将在下文中详加讨论。不过,截至目前,其职责和能力仍不够明朗,因此,以此为基础提出空天战争理论显然为时过早,而着手制定相应的防御措施就更不合时宜了。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将那些武器视为空天攻击手段都过于牵强:除了较短的助推阶段以外,其整个弹道都处于大气层上部,其速度也介于飞机和弹道导弹之间。因此,与其说这一类系统属于天基武器,倒不如说它们更像是传统的远程弹道导弹。最后,那些在理论上可对地面、海上和空中目标予以打击的天基武器其实并不存在,并且其未来的生存能力仍不够明朗。
即使空天战争的概念仍不够明确,但提出这一概念的军事和技术专家却就发起这一战争所需的能力达成了一个可预测的结论。他们通常认为,俄罗斯需要“利用空天防御系统来反击空天攻击系统。…… 一个有望摧毁并压制空天攻击手段的系统应该能够发挥反导弹、反卫星、防空导弹、空中作战单位和无线电电子战部队的协同效应。它的构成体系应该包含多个层次”。[9]
这种呼声正逐步转变为特定的政策。最值得注意的是,空天防御项目(军方高层领导人和军工集团正致力于为这些计划四处游说)在截至2020年的国家军备计划中占据了最重要的比重,在2011年首度公布这一项目时,它在所有经费中所占的比重为20%左右,大约为3.4万亿卢布(当时约合1060亿美元)。[10] 伴随着新型“沃罗涅日”型陆基雷达和导弹发射探测卫星的开发和部署及其推动的导弹预警系统的现代化进程,该项目计划部署28个配备S-400“凯旋”防空导弹系统的团级部队(拥有大约450至670个发射器)以及38个配备新一代S-500“勇士”防空导弹系统(最近已更名为“Prometey”)的营级部队系统(拥有300至460个发射器)。[11] 总的说来,该计划将制造共计3000枚两种型号的拦截导弹,并将为此新建三家生产厂。一个全新的一体化全自动指挥和控制系统正在创建之中,其目的是为了促进空天防卫部队的作战行动。俄罗斯的现代化A-135导弹防御系统(现已更名为“A-235”)将被纳入非核动能拦截导弹,以便拦截来袭的导弹(此前的拦截导弹通常配备的都是核弹头)。[12] 俄罗斯目前的经济危机导致2017财年的国防预算大幅削减,这很可能会延缓空天军备项目的进度并缩减武器采办的规模,但潜在的势头将不会受到影响,除非俄罗斯防御姿态的重大变化迫使其被中途叫停或重新定向。
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俄罗斯的空天战争战略都与交缠问题具有直接的关系。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俄罗斯的政策可以被视为军方渴望打破僵局(即共同核毁灭原则的“遏制效应”)的本能需求,这也导致武器得到进一步发展,高科技竞争日趋激烈以及令人不敢轻举妄动的世界大战情境变得毫无意义(事实上,正如当时的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曾指出的那样,它促使上世纪70、80年代的美国和前苏联领导人达成了“永远不打那种谁也打不赢的核战争”的一致意见。[13])在冷战持续的40年期间,前苏联连续数代军事和国防精英已经了解并习惯于与最强大的竞争对手——美国——你争我夺的局面,而这样的竞争已经成为了他们坚持下去的理由。冷战的结束以及上世纪90年代早期的核军备竞赛剥夺了他们的光荣使命,而敌对势力组成的流氓国家和恐怖分子却令他们面临更加惨不忍睹的局面。不过,美国和北约在前南斯拉夫和伊拉克的作战行动带来了一项全新的高科技挑战,俄罗斯人称之为“空天战争”,这一概念立即被视为与富有价值的对手之间极具吸引力且毫无限制的全新竞争领域。此外,这一战争的全新维度无疑还为军方及与之相关的国防工业提供了以新出现的秘密威胁说服政治领导人的契机,同时也为国防事业、武器采办项目和庞大的国防预算占据优先次序提供了充分的理由。
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俄罗斯的空天战争战略都与交缠问题具有直接的关系。令人惊讶的是,这使得这一概念看起来更富有学术内涵,提出这一概念的人并未揭示一个最重要的问题:空天战争的背景究竟是一场全球性的(或区域性的)核战争,还是一场迫使俄罗斯与美国和北约紧张对峙的非核战争?
如果是前者,那么在大规模使用配备核弹头的弹道导弹的情况下(如果缺乏有效的导弹防御系统的话),俄罗斯空天部队就不太可能发挥有效的作用。除了就来袭导弹的攻击行动发出警告以外,俄罗斯空天部队将无法完成俄罗斯军事理论为其分配的任务,包括“反击空天攻击行动,以及保卫俄罗斯的高级指挥所和军事指挥部门、战略核部队各单位和导弹警报系统的各个作战小组”。[14]
而如果空天战争涉及非核冲突,那么这一概念就将引发性质截然不同的严重质疑。俄罗斯政府和军方领导人经常谈及通过非核手段赢得大规模冲突的惨烈情境。例如,前国防部副部长阿尔卡季·巴辛(Arkady Bakhin)将军就曾直言,“世界强国都不惜一切代价想要获得空中和太空领域的制胜权,在战争爆发时开展大规模空天作战行动,并在全国各地针对至关重要的战略要地发动打击行动。”[15] 不过,我们仍然很难乐观地预测,在现实中,这样的冲突不会迅速升级为核危机(尤其是战略部队及其指挥、控制、通信和信息系统不断遭到常规弹药攻击的情况下)。
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前苏联的军事领导人才相信,“一旦(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收到关于北约正准备发动核打击的消息后”,这些国家就将首先使用数百枚战术核武器,而一场大规模的欧洲战争终将在所难免。[16] 随后,前苏联军队将在几周内抵达英吉利海峡和比利牛斯山脉,否则前苏联和美国就将对对方开展大规模的核打击,而战争将在几小时内(或者在几天之内)结束,伴随而来的是灾难性的后果。[17]
冷战结束后,确定可能的大规模战争情境的任务实际上已经被束之高阁,因为在全新的政治环境中,这一类战争是无法想象的。不过,关于新一代高科技全球战争的战略思想显然仍处于隐秘的发展阶段(而且可能不仅仅只限于俄罗斯地区)。目前,在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展开新一轮交锋的阶段,这项工作的成果终于迎来了曙光。总的来说,战略决策者认为,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可能是数日或者数周的时间),西方国家将在不使用核武器的情况下针对俄罗斯发动空袭和导弹攻击行动。而反过来,俄罗斯将针对这种攻击采取防御措施,并利用远程常规武器进行报复性打击。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国防部部长绍伊古(Shoigu)曾于2016年指出:“截至2021年底,我们计划将全国战略非核部队的战斗力增至四倍,这些作战人员将有望全面执行非核威慑任务。”[18]
换言之,基本的前提就是,由美国领导的针对前南斯拉夫(1999年)和伊拉克(1990年和2003年)的战略(这一领域内的专家经常以此为例)可能会被用来对付俄罗斯,但得益于俄罗斯空天部队、战略火箭部队和海军部队针对美国及其盟国的作战行动,其产生的结果将截然不同。
对防御性和进攻性战略非核武器的重视并不排斥(反而需要)在武装冲突的某一时刻使用有限的核武器。锦旗设计局(该机构主要负责战略防御系统的设计工作)的总设计师、俄罗斯国防工业最具权威的代表人物之一谢尔盖·苏克哈诺夫(Sergei Sukhanov)曾透露俄罗斯当代战略逻辑关于进攻系统与防御系统以及核系统与非核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的概要情况:
如果我们不能排除美国及其他北约国家组织大规模空天攻击的可能性(即,如果我们面对上述国家将针对前南斯拉夫的战略应用于俄罗斯的情况),那么,我们显然不可能通过在空天领域内利用毁灭性武器并抵御空天攻击来解决相关的问题,因为这需要在整个俄罗斯境内创建高效的空中和导弹防御系统。因此,在这种可能的情况下,应对空天防御任务的战略应以遏制敌方的大规模空天攻击为基础,这主要是通过实施足以避免升级并可以迫使敌方放弃进一步空天攻击的大规模核威慑来实现的。[19] (重点标识由作者所加。)
换言之,苏克哈诺夫认为,由于俄罗斯的能力在抵御空天攻击这一方面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俄罗斯必须使用有限的核武器来迫使美国及其盟国作出让步。这一基本逻辑在俄罗斯被广泛接受。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美国并没有(在可预见的未来也不太可能采取)任何技术手段或作战行动来对俄罗斯发动非核空天战争。不过,事实上,在俄罗斯当代的战略思想家看来,俄罗斯与美国和北约成员国之间的大规模战争是涉及核任务和非核任务、防御和进攻能力以及弹道和空气动力武器系统的一体化技术和作战系统的长期行动,这一事实是催生交缠的基础。其结果很可能导致局部非核冲突迅速升级为全球核战争。本章的其余部分将针对“全新和新近出现的军事技术是如何导致这种升级的”展开讨论。
非核战略武器与交缠
第一种(同时也是最有可能出现)的交缠类型就是战术核武器与非核武器之间的相互作用。在常规冲突中,战术核武器很可能存在意外遇袭的风险,因为它们的运载工具往往与常规部队和武器位于相同的军事基地内(并且往往可以同时使用)。此外,它们还需要用到由海军、空军和地面部队操作的两用运载工具(其中就包括由地面部队操作的“伊斯坎德尔”和“圣甲虫”陆基导弹系统、海军旗下的“口径”海基巡航导弹以及海军和空军旗下的中型轰炸机和战术攻击机)。此外,海军和空军基地的指挥所和战术核武器军械库更有可能成为非核攻击系统蓄意打击的目标。
第一种(同时也是最有可能出现)的交缠类型就是战术核武器与非核武器之间的相互作用。
当然相反地,战术核武器也可以被用来打击非核目标。战术核武器可有效地打击地面部队的集结区和基地以及机场、海军基地、潜艇和水面舰艇。这种用途可能会引发针对海军基地和机场的核报复。此外,俄罗斯还曾公开宣称,加里宁格勒地区配备核弹头或常规弹头的陆基“伊斯坎德尔”导弹可以用来攻击美国部署于欧洲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特别是部署于波兰境内的标准三型拦截导弹的发射器及与之相关的雷达系统(通常称为“陆基宙斯盾系统”)。[20] 就俄罗斯和北约提出的全新战略概念(即,在旨在促成降级的非核冲突中首先使用核武器)而言,这种风险尤其高。[21] 事实上,使用核武器的这种情况很可能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从而引发迅速升级并造成毁灭性的后果。
不过,已经有大量科学和政治分析人士针对战术核武器这一专题进行了探讨。本分析报告接下来将从战略进攻和防御武器系统及其指挥、控制、通信和信息系统的角度来探讨关于交缠的问题。
针对非核威胁作出响应的有限战略打击(即,利用洲际弹道导弹、海基弹道导弹和重型轰炸机的有限打击——最有可能是针对美国本土的打击行动)代表了另一种形式的交缠。俄罗斯的军事理论保留了使用核武器作为应对措施(基于俄罗斯的存亡受到威胁时,其他国家使用非核武器侵略俄罗斯联邦的前提)的权利,不过(正如其他拥核国家的理论一样),俄罗斯并未明确界定“俄罗斯的存亡”的定义,也并未就使用这一类核武器的规模作出界定。[22] 目前,在俄罗斯或美国政府有关这一话题的官方文件中,并未有任何公开提及有限的战略核打击的信息。尽管如此,国防部智囊团的部分军事专家仍然在其撰写的著作中透露了只言片语。例如,一些俄罗斯专家曾指出:
其主要特点就是初始核影响的有限性,其目的在于震慑(而非伤害)侵略者,迫使其停止攻击并开始谈判。我们认为,如果缺乏这一类响应措施,那么所部署的核武器的数量和当量都将大幅提升。因此,我们预计,俄罗斯联邦第一次使用的核武器将是有限的。据推测,对手的响应措施则很可能是大规模的核打击或有限的核打击。我们认为,第二种可能性更大。毕竟,美国正是首度提出有限核战争这一概念的国家。[23]
我们有理由认为,美国的战略思想家们采纳了“有限的核使用及量身定做的核方案”的概念并阐述了类似的理念。[24]
这些概念仅仅是推测,同时也具有一定的风险。如果在危机中向过度自傲、缺乏经验并且缺乏战略头脑的领导人提出这一概念,那么它很可能会成为灾难之源。与“使用战术核武器来促使俄罗斯与北约之间的常规局部战争降级”这一重获重视的概念一样,它们是当代军事战略中风险最大的创新,极有可能导致灾难性的交缠结果。
一个持久的观念(即,针对俄罗斯军用核设施的关键据点使用高精度非核武器组织大规模毁灭性打击行动的现实可能性)已在俄罗斯领导人中(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专家群体中)中逐步成形。这是上文中曾讨论过的空天战争理论的一大要素。
甚至连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总统也表达了担忧之情。在2015年参加瓦尔代辩论俱乐部的一次演讲中,他曾指出:“所谓的第一轮毁灭性打击(包括使用高精度的远程非核武器)的战略已经成形,其效果完全可以与核武器相提并论。”[25] 一年前,在讨论削减核武器的可能性时,普京总统还提到了这一令人担忧的问题:“时至今日,多种高精度(非核)武器的能力已经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非常接近,如果完全放弃或大幅削减核武器,那么研发和制造高精度系统的领先国家将拥有明确的军事优势。”[26]
副总理德米特里·罗戈津(Dmitry Rogozin)也曾发表类似的评论,他指出,高精度常规武器的打击行动很可能会在几个小时内摧毁俄罗斯90%的战略部队。[27] 此外,负责设计和制造防空系统的军事工业企业——阿尔马兹-安泰集团的总设计师帕维尔·索辛诺夫(Pavel Sozinov)也以更详细的细节阐述了这一威胁:“现在的主要威胁就是在进攻早期大规模使用巡航导弹。……根据主要针对其海上部队的重整军备计划,美国将在2015年至2016年期间拥有大约6500-7000枚巡航导弹,这些导弹可以用来攻击俄罗斯联邦的关键据点,其中大约5000枚导弹将从海上发射。……在军事行动的第一阶段如此大规模地使用巡航导弹很可能会对俄罗斯的战略核基地造成巨大的破坏。”[28]
美国和俄罗斯的能力
美国的亚音速巡航导弹:无论是从质量还是从数量来看,美国目前已毋庸置疑地成为了高精度非核巡航导弹的领先国家。光美国海军就已经拥有了超过600枚“战斧”对地攻击导弹部署在四艘俄亥俄级核动力巡航导弹潜艇上(每艘潜艇分别携带154枚导弹);500枚导弹(分别部署于25艘弗吉尼亚级和海狼级攻击核潜艇上);以及4560枚导弹(分别部署于22艘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和62艘阿利·伯克级驱逐舰上)。根据未经证实的报道,截至2020年,美国可能将一共部署大约6300枚“战斧”巡航导弹。改进这种武器的工作仍在继续。例如,2014年,美国空军就曾宣布,计划采用一种新型空对地巡航导弹——AGM-158B增程型联合防区外空对地导弹(俗称“JASSM-ER”)。[29]
俄罗斯的亚音速巡航导弹:面对这一现实,俄罗斯正致力于大幅扩充其高精度巡航导弹的武器库。目前,俄罗斯正使用可配备核弹头和非核弹头的远程导弹,包括Kh-55SM导弹、多种改良版“口径”导弹以及全新的Kh-101/102空射型巡航导弹。目前无法获得关于俄罗斯制造的巡航导弹总数的公开资料。不过,在2013年,谢尔盖·绍伊古(Sergei Shoigu)的确曾宣布,在俄罗斯武装部队服役的巡航导弹的数量将分别在2016年和2020年增至5倍和30倍。[30] 2014年,俄罗斯开始着手改装纳希莫夫海军上将号核动力重型巡洋舰,目的是为了将其改装为俄罗斯第一艘配备远程高精度巡航导弹的舰艇。这一举动表明,俄罗斯正致力于实施发展非核战略威慑能力的战略(正如2014年12月俄罗斯批准的全新军事理论所规划的那样)。[31] 无论当前的经济危机将在多大程度上对这些拟议计划的实际执行情况产生影响,这一地区都已经出现了军备竞赛的明显迹象。
“高超音速武器”这一术语通常包含两种不同的技术: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和助推滑翔武器。一些发达国家(包括俄罗斯和美国,后者最近刚刚针对X-51A原型进行了测试)正在开发前一种导弹。
与高超音速巡航导弹相比,高超音速助推滑翔武器可以更快的速度飞行更远的距离,从战略角度来看,后者也更加重要。目前对其进行开发和测试的国家主要包括中国、俄罗斯和美国。这些导弹旨在在相当短的时间内(与现有的亚音速巡航导弹相比)对各种目标发动高精度打击。
美国的助推滑翔武器:在过去十年间,美国一共组织了两次洲际高超音速助推滑翔飞行器的飞行试验。其中一组试验中涉及第二代高超音速技术飞行器(HTV-2),洛克希德·马丁空间系统公司于2003年开始研发这种滑翔器,其影响范围将遍及全球。该滑翔器分别于2010年和2011年进行了两次测试。但两次都由于不同的问题而在气动飞行测试不足三分钟时提前终止了试飞活动。虽然这一项目尚未完全终止,但其当前的融资水平已经非常低,并且目前并未针对其飞行测试制定进一步的计划。
而先进高超音速武器(AHW)项目则取得了更大的进展。该项目旨在研发出射程可达大约8000公里(约5000英里)的滑翔器,并已进行了两次测试。美国国防部表示,2011年首次飞行3800公里的测试已经取得了成功。在2013年飞行距离更长的第二次测试中,由于增压器故障,试飞活动在气动飞行前就失败了。据估计,该系统将进行进一步的飞行测试。迄今为止,美国国防部仍未宣布部署该系统的任何计划。
前苏联和俄罗斯的助推滑翔武器:俄罗斯于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启动了第一个高超音速系统的开发项目和飞行测试,该项目可能是“信天翁”项目的一个子项目(该项目在后期报告中的代号为4202)。正如许多其他领域一样,这一领域的大量工作也是因里根于1983年公布的《美国战略防御计划》(SDI)而推动的。《美国战略防御计划》提出了一个包含太空、空中、海上和陆上部队的多层弹道导弹防御系统,以便抵御前苏联的大规模弹道导弹攻击。
前苏联针对《美国战略防御计划》采取了一系列对称和非对称的对抗措施。“信天翁”项目属于后者。尽管俄罗斯媒体最近已经打探到了有关该系统各种版本的信息,但关于该项目的细节仍属于机密信息。[32]
根据这些信息,在政府颁布法令后,机械制造科技生产中心于1987年开始着手研发真正的导弹系统。从理论上说,研发该系统的目的在于利用使用液体燃料的UR-100N UTTKh(SS-19)洲际弹道导弹将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推送到太空中,随后,它将加速返回地球并以高超音速在初始海拔高度为80至90公里(大约为50至55英里)的高空进行远距离滑翔。配备一枚核武器的滑翔器可以高速进行跨洲际飞行,以便避开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监测。据报道,“信天翁”的第一次飞行测试于1991年至1992年[33]启动。根据媒体的报道,2001年至今已经组织了多次进一步的测试。据悉,这些测试涉及从发射井发射的UR-100N(SS-19)导弹(由于滑翔器的尺寸过大,导致其中部分舱门无法关闭)。各种在三级固体推进剂导弹上部署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的计划(包括通用型洲际弹道导弹(在开发阶段即被叫停)和Topol-M(SS-27)洲际弹道导弹)均未能实现。最近,有报道称,滑翔飞行器可以被部署到新一代的Sarmat RS-28液体燃料重型洲际弹道导弹之上。[34]
与这些消息相反的是,规避陆基导弹防御系统的机动行动很可能并不是“信天翁”滑翔器的主要目的,这主要是由于在穿越大气层时,其速度将明显降低,使其极易被美国的“爱国者”防空导弹拦截。相反,其飞行轨道很可能是为了减少《美国战略防御计划》所规划的天基导弹防御系统拦截再入飞行器的可能性。
目前,我们仍未能获得关于如何在“信天翁”项目中开发这一类滑翔器并在其弹道末段减速过程中击溃陆基导弹防御系统的信息。从开源信息渠道来看,目前尚不清楚俄罗斯的高超音速助推滑翔武器是否将装备常规弹头或核弹头来应对俄罗斯军事理论[35]中所指的常规威慑目标。如果是后者,那么这些武器的主要目的就是确保有限的打击行动(甚至也许只是一种武器)能够突破美国未来的导弹防御系统。[36]
非核武器的毁灭性打击效能
非核武器的毁灭性打击威胁是俄罗斯的专家和政府官员争论不休的核心话题之一。考虑到美国开展后续核报复的确定性,俄罗斯政府很可能不愿意利用核武器进行反击,而美国是否会针对俄罗斯发动大规模的常规打击(其效能必将比核打击低得多)就成为了争论的关键要点。一个值得关注的特定问题就是,美国可能会将俄罗斯对常规毁灭性打击威胁的重点关注视为俄罗斯政府不愿意使用核武器来对抗这种攻击的证据,从而促使美国利用这一类常规空袭行动来赢得局部或地区冲突中的升级优势。
不过,与这样的战略考虑相反的是,在现实中,一旦美国针对俄罗斯的核部队发动作战行动,则俄罗斯政府很可能会在早期利用有限的战略核打击进行报复(基于俄罗斯的“遇袭即发射”原则)。另外,俄罗斯政府甚至还可能抢在美国前发动特定的战略核打击,以便阻挠实施常规打击并被视为常规攻击部队的美国海军和空军部队;这主要是通过针对机场、海军基地及后者的指挥、控制、通信和信息设施发动攻击来实现的。在后一种情况下,俄罗斯政府甚至期望美国在其领土受到核攻击后,仍然有选择性地采用“适度的战略方案”来作出回应。事实上,美国的应对措施很可能是针对俄罗斯发起大规模核攻击,从而引发大规模的核交锋。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俄罗斯政府越是担心其核部队的生存能力,则冲突越有可能进一步升级。
一旦美国针对俄罗斯的核部队发动作战行动,则俄罗斯政府很可能会在早期利用有限的战略核打击进行报复。
非核武器的毁灭性打击目标可能包括:各级部队极其坚固的指挥中心、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井、陆基移动式导弹的轻型军用方舱、暴露在战区野外的机动洲际弹道导弹发射器、基地内的弹道导弹核潜艇、主要机场和备用机场的重型轰炸机、陆上通信基地、预警雷达、用于导弹预警系统指挥中心以及核武器军械库。
这些目标的脆弱性取决于其防御和隐蔽的方式以及应对来袭武器的有效性。早期预警雷达、移动式洲际弹道导弹发射器的轻型军用方舱、基地内的导弹潜艇、机场的重型轰炸机以及指挥、控制、通信和信息中心和非深埋式基地被拥有足够射程和定位能力的攻击武器摧毁的可能性较高。
如果俄罗斯和北约在东欧或北极地区爆发局部或地区性的常规冲突,那么针对这些据点的空袭和巡航导弹攻击就很可能导致核战争迅速升级。美国针对这一类目标的早期攻击很可能并非蓄意为之,因为俄罗斯的战略潜艇和轰炸机与常规海军舰艇和飞机均位于同一基地,而针对后者的攻击可能会意外摧毁前者。与中国政策背后的逻辑所不同的是,前苏联和如今的俄罗斯将核部队和常规部队部署于同一据点的作法是出于经济和行政方面的考虑,而不是试图通过核威胁升级来阻止美国针对俄罗斯常规部队的非核打击这一战略目标。
在常规冲突中拦截正执行飞行任务的重型和中型两用轰炸机同样会导致不可避免的交缠。这些轰炸机可能参加常规的任务,但也可能奉命携带核武器执行巡逻任务,以便在冲突升级时提高其生存能力。如果这些携带核武器的飞机被摧毁,那么就很可能引发冲突升级的危险。常规威胁也可能会对俄罗斯部署于北极、北大西洋和太平洋地区的核弹头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潜艇造成类似的风险。
俄罗斯国内对于加固据点(例如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井)的生存能力存在比较严重的争议。虽然俄罗斯的官方立场认为,这些据点可能会受到非核武器的威胁,但仍有一些分析人士(包括国防部研究所的专业人士)并不认同这种观点。例如,一篇文章就基于下列理由驳斥了“使用非核弹头亚音速巡航导弹攻击洲际弹道导弹发射井可造成有效的毁灭性打击”的观点:[37]
- 在一场针对加固据点的打击行动中,核武器和非核武器的破坏力是无法相提并论的。这意味着,必须使用大量非核武器才能达到效果。
- 如果想要干扰巡航导弹制导系统并降低导弹的效能,就需要进一步增大非核武器的数量,同时还要求侵略者集结大量巡航导弹及其运载平台。
- 要想针对俄罗斯在其广袤的国土上部署的数百个目标同时制定出这一类打击计划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从不同地点发射的导弹将不可避免地在不同时间击中目标,而俄罗斯则有机会在被彻底摧毁前至少发射出一枚核武器)。
- 我们有必要评估打击行动的结果,并在必要时重复这一步骤。
- 使用巡航导弹来开展的作战行动不太可能在一波攻击中(甚至在一天的攻击中)就完成任务,这将在进攻过程中为俄罗斯提供报复的机会。
- 需要很长时间才能为这一类作战行动集结到足够的兵力。这样的准备工作是无法悄然进行的,这将为俄罗斯的核武器、预警系统和指挥系统进入高度警备状态提供足够的时间。
从黑海发射的巡航导弹可针对俄罗斯部署于塔季谢沃的大约90个洲际弹道导弹发射井同时发起攻击,笔者引用了关于其攻击效能的计算结果。要确保对发射井的命中率达到95%,就需要14枚巡航导弹的精确度(圆径概率误差)为5米。8米的精确度需要35枚导弹,这就意味着,仅仅针对一个部署区就需要使用3150枚巡航导弹。此外,许多其他洲际弹道导弹的部署区已远远超出了海基巡航导弹的射程。美国所拥有的巡航导弹并不足以针对所有这些目标同时发动攻击,而在可预见的将来也无法实现这一目标。
俄罗斯还试图利用防御系统和进攻性非核武器来推迟必要的核报复(至少在空天战争的初期阶段内)。
事实上,还有许多其他措施可以用来应对巡航导弹的攻击:在高风险时期,可以经常更换移动式洲际弹道导弹发射器的基地;可以部署与真正的洲际弹道导弹发射器极为相似的虚假目标;战略导弹潜艇可奉命执行海上任务并由其他海军部队提供保护;轰炸机可以分散部署并进入机场或空中警戒状态;固定的战略据点可以高效的Pantzir-S2近程高射炮和导弹系统以及其他空中和导弹防御系统作为配合防守的系统。
美国利用巡航导弹发起毁灭性打击的行动不会成功,加之其缺乏足够导弹的事实,导致俄罗斯领导人对这一担忧的合理性备受质疑。不过,这些担忧可能是出于对俄罗斯是否有可能以大规模核反击威胁阻止这种打击的质疑,毕竟,这种应对措施势必会招致美国大规模的核报复。因此,俄罗斯政府对传统还击能力的担忧依然不减,俄罗斯十分重视空天防御、常规威慑和有限的核打击方案并希望这些方案能迫使美国政府停止战斗并开始谈判(而不是引发美国的大规模核报复)。
因此,俄罗斯阻止巡航导弹反击的战略并不依赖于快速升级至核战争的威胁(这可能是中国的做法)。相反,俄罗斯还试图利用防御系统和进攻性非核武器来推迟必要的核报复(至少在空天战争的初期阶段内)——无论如何,这正是空天部队的理论所假设的情况。不过,实际上,冲突的实际发展趋势可能与俄罗斯所希望的南辕北辙。特别是,如果俄罗斯在某个阶段对美国发动有限的核打击,那么美国是否会采取有限的核对策仍未可知。
展望未来,俄罗斯的领导人对高超音速武器是否会增强敌方使用常规力量打击军事目标的能力非常担心。从政治和军事方面来看,考虑到俄罗斯的报复性核打击所带来的极高风险,美国使用非核高超音速系统对战略军事目标进行打击的可能性似乎并不大。尽管如此,与现有的武器相比,从纯技术的角度来看,高超音速武器仍将具有一定的打击军事目标优势。
俄罗斯和美国正在研制的高超音速巡航导弹的速度要比现有的巡航导弹快得多。虽然在很远的距离外即可探测到这些导弹(得益于其飞行的高度),但它们的速度使得防空系统和防空战斗机的拦截任务变得异常困难。
对战略目标的潜在威胁主要是来自助推滑翔武器。助推滑翔系统可以解决或缓解与现有的亚音速巡航导弹有关的一些难题:
- 在美国部署洲际滑翔器将大幅减少发动攻击行动所需的准备时间,同时还使得此类准备工作更不易被俄罗斯察觉。
- 助推滑翔武器可以比现有巡航导弹更快的速度击中目标(从美国大陆发射的助推滑翔武器可在40至60分钟击中目标,而由非核潜艇发射的亚音速巡航导弹则需要两小时至两个半小时)。第一波攻击的持续时间也会短得多。
- 由于拦截系统拦截这些导弹的能力将会有所削减,因此,所需的导弹数目也更少。
助推滑翔武器还具有比弹道导弹更多的优势。可以肯定的是,当代的战略陆基和海基弹道导弹(目前均配备了核弹头)可以比助推滑翔武器更快的平均速度飞行,其飞行时间也更短。此外,尚不存在针对大规模弹道导弹攻击的有效防御能力。不过,助推滑翔武器的精确度可能更高。弹道导弹采用的是惯性制导(在某些武器中利用天文导航系统加以补充),这通常可提供100米到200米的精确度——这种精确度只要为它们配备核弹头就够用了。相比之下,助推滑翔武器所利用的则可能是外部导航信号(例如由全球定位系统产生的信号),同时还可能拥有末端制导的功能(例如地形匹配)。
更重要的是,在弹道导弹和助推滑翔武器的轨迹之间存在关键性的差异。弹道导弹的轨迹是可预见且易于观测的。在其发射后的最初几分钟内,预警卫星就能探测到其飞行轨迹。随后,在弹头撞击前10至15分钟,其轨道可以由导弹预警雷达予以确认。至少从理论上来说,这些特性使对手的导弹防御系统有机会拦截到位于轨道中段或末端的来袭导弹。更可能的情况就是,在侵略者核弹被引爆前,它们为对手提供了进行报复性打击的机会。
与弹道导弹类似,卫星同样可以探测到助推滑翔武器的踪迹。不过,它们随后将进入大气层并沿不可预知的轨迹、以超音速且远低于洲际弹道导弹或海基弹道导弹的高度飞行。得益于其飞行高度,助推滑翔武器的行踪几乎完全无法被导弹预警雷达侦查到,从而导致预警时间大幅缩短。导弹预警雷达也许只能在撞击前三、四分钟才能探测到来袭的助推滑翔武器,而防空雷达则只能在撞击前三分钟内才能探测到它们。[38]
要想探测到这一类攻击并有足够的时间来跟踪并拦截导弹,俄罗斯将不得不大幅改良其预警以及指挥和控制系统,并大量部署全新的拦截系统(例如:S-500和Pantzir-s2防空系统),而这必将耗资不菲。
虽然在检测和拦截助推滑翔武器时将面临重大的挑战,但在配备非核弹头的情况下能否保障足够的精准度来摧毁加固的洲际弹道导弹发射井和指挥中心却仍未可知。与此同时,攻击移动式陆基系统需要在最后阶段对来袭导弹的轨道进行航向修正。如果所需的信息是通过卫星或飞机而获得的,那么这就会产生防御方可加以利用的漏洞(例如:防御方可以利用无线电电子战干扰卫星信号)。此外,自主末端制导功能还可能需要助推滑翔武器来大幅减速,这将为防御方提供实体拦截的机会。
最后,目前尚不清楚:美国是否愿意为了对俄罗斯的战略威慑构成威胁而花费巨大的代价制造数量众多(高达数百枚)的助推滑翔导弹。部分俄罗斯专家认为,这一类导弹(即使数量有限)可以用来袭击莫斯科的重要指挥中心及其他安置国家领导人的据点。不过,这种担心是没有根据的,因为俄罗斯战略核部队冗余的指挥和控制系统很难被摧毁。事实上,部分指挥中心已经被加固,因此,它们可以经受得住直接的核打击——即使面对高精度常规弹头的打击亦无需担忧。
即便如此,俄罗斯的军事和民防官员仍不得不考虑最坏的情况。特别是,助推滑翔武器的轨道将令在遇袭时即发射洲际弹道导弹的行动变得异常艰难(“遇袭即发射”依然是俄罗斯在大规模核战争中的主要(但并非唯一)作战理念以及评估其战略力量的充分性的主要标准)。地面雷达只能在稍晚的飞行阶段才能探测到来袭的滑翔器,事实上,这对于在遇袭前发射洲际弹道导弹的行动已为时晚矣。因此,只要在卫星探测到发射助推滑翔武器的行动后,就可以执行“遇袭即发射”方案,而不需要地面雷达对攻击行动予以确认。
顺便说一句,如果滑翔器配备了核弹头的话,则助推滑翔武器针对俄罗斯战略部队的攻击将更加有效。出于这个原因,俄罗斯政府高度怀疑美国将为其助推滑翔系统配备核弹头,尽管在冷战结束后,美国从未公开讨论过这一概念。即便如此,无论助推滑翔武器将配备何种武器,相关技术的面世(及其对俄罗斯核部队所构成的威胁)都将大幅增加因预警卫星发出虚假警报而导致核战争的可能性。这种危险很可能是由助推滑翔武器而引起的最大风险。
俄罗斯正针对高超音速武器产生的威胁作出响应。S-500防空体系(正处于开发阶段)的研发目的正是为了保护战略核据点免受未来的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和火箭助推滑翔武器的攻击。为此,它们将与天基和陆基导弹预警设备一起被整合到一个统一的指挥、控制、通信和信息系统中。为了保护俄罗斯的军事和政治领导人免受弹道导弹和非核助推滑翔武器的伤害,俄罗斯正在升级莫斯科的A-135导弹防御系统并部署S-400防空系统(计划在未来部署S-500防空系统)。
所有碰撞杀伤型非核弹道导弹防御系统都将加剧俄罗斯政府对美国非核攻击系统的担忧。最简单的假设场景是,美国将通过常规的打击军事目标行动来摧毁绝大部分的俄罗斯战略部队(如上所述,罗戈津苏所提及的比例为90%)。如果剩余的部队全部幸存下来的话,那么将有50至60枚导弹被美国及其盟国部署在欧洲、亚洲、阿拉斯加以及加利福尼亚(未来还可能部署于美国东北部的某个据点)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拦截。据俄罗斯估计,目前,美国拦截导弹的数量大约为300多枚,包括部署在美国本土的地基拦截导弹、部署在世界各地的末段高空区域防御系统(THAAD)拦截导弹以及部署在欧洲境内和舰艇上的标准三型拦截导弹。截至2020年,其总数预计将超过1000枚。[39] 一个更复杂的问题就是,尽管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将无法阻止俄罗斯大规模的导弹攻击,但美国仍然能够阻止特定或有限的战略打击(这被俄罗斯视为针对常规空天攻击的应对措施)。俄罗斯未来的常规或核助推滑翔系统被视为突破这一类防御系统的潜在手段,这将进一步模糊常规战争与核战争之间的界线,并加剧交缠的风险。
目前,俄罗斯对美国战略要地发动非核打击的能力仍远远落后于美国以非核手段瞄准俄罗斯同类据点的能力。
目前,俄罗斯对美国战略要地发动非核打击的能力仍远远落后于美国以非核手段瞄准俄罗斯同类据点的能力。俄罗斯的能力范围主要覆盖美国的欧洲和亚洲的盟友以及特定的目标,例如:美国的战术核武器库、包括雷达和发射器在内的导弹防御部队、关键的工业基地、以及英国和法国的战略部队(特别是部署在基地的潜艇和飞机)。
尽管针对部署在英国、格陵兰岛和阿拉斯加的雷达(这些雷达可以针对导弹攻击提供预警并为弹道导弹防御任务提供支持)以及其他一些战略据点的选择性打击是可行的,但这仍将令俄罗斯的重型轰炸机、核动力攻击潜艇及其他舰艇(作为高精度常规巡航导弹的投射平台)很难突破美国及其盟国的防御系统。俄罗斯仍有很大的机会使用高超音速武器对敌方造成损害。如果这些系统配备了非核弹头,那么很可能会导致交缠并促使冲突升级为核战争。
反空间武器与交缠
除了针对对手在陆地和海上的核部队及其辅助性基础设施开展的高精度常规攻击以外,在局部或大规模常规战争中使用配备非核弹头的反卫星武器(这些武器可以针对卫星发起攻击,而这些卫星正是对手的战略指挥、控制、通信和信息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对交缠构成最大的威胁。
军用卫星在各种轨道上运行。其中约有25%的卫星(包括许多情报、监视和侦察卫星)均位于近地轨道,另有20%(包括导航卫星)则位于中地球轨道。剩余55%的卫星(包括预警和战略通信卫星)则在高椭圆轨道和地球静止轨道上运行。绝大多数国防航天器都属于美国;美国军事太空计划的经费已大大超过了所有其他设有类似项目的国家的经费总和。[40]
航天系统已经成为全球各大强国的武装部队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没有这些系统,这些国家几乎无法开展任何军事行动(至少在当今的世界中,其军事行动的效能将大幅削弱)。为军事行动的效能作出最大贡献的天基系统就是信息和通信系统。
美国和俄罗斯的能力
美国的反卫星计划:美国于1957年正式启动了有关反卫星技术的研发工作。1963年,两座太平洋岛屿上的核武器拦截系统(最初以奈克-宙斯反弹道导弹为基础,随后改为“雷神”导弹)进入戒备状态。1974年,这些拦截系统退役并被封存。
1977年,美国通过开发迷你空射型系统(MALS)及其他举措,重新启动了反卫星武器的计划。这种由F-15战斗机发射的导弹可以携带一驾小型自动导引型飞行器,其目的旨在在海拔大约1000公里(高于600英里)的高空摧毁卫星。在1984年至1986年期间,该系统进行了飞行测试,其中包括对太空中实体目标的一次测试。俄罗斯预计,美国可以在24至36小时内利用该系统击中在近地轨道上运行的三枚卫星。1988年,迷你空射型系统项目被取消。俄罗斯政府认为,在当代,要想将这一套系统投入使用,需要长达数月的筹备时间。
1989年,美国开始启动陆基反卫星系统(即,动能反卫星项目)的研发工作。它被称为“生态友好型”项目,因为其目的旨在尽量减少产生轨道碎片的风险。俄罗斯认为,这一系统是为了在一周内摧毁所有近地轨道的军用卫星。该系统并未真正投入使用,尽管美国制造了三套拦截系统,但其资金却最终在本世纪初逐步枯竭。
美国还测试了中红外先进化学激光器作为反卫星武器的能力,这一陆基激光系统位于美国陆军的白沙导弹试验场(位于新墨西哥州)。1997年10月,该系统被投入测试,据报道,它曾摧毁了一台海拔420公里(约260英里)的卫星传感器。[41]
在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总统执政期间,美国对反卫星技术的兴趣再度高涨。美国为轻型激光器(包括在空间内可行的部署方案)的研发项目提供了资金。此外,在小布什总统执政期间,美国的导弹防御计划进一步扩大规模,这些计划帮助美国发展了重要的反卫星能力,即使美国政府矢口否认他们正在推进这些计划(这至少是美国拒不承认发展反卫星能力的部分原因)。例如,可在助推阶段拦截弹道导弹的机载激光器(包括一台安装在波音747飞机上的强大的激光器)可以被用来攻击近地轨道的卫星。这一系统针对弹道导弹的能力在多种测试中都取得了成功,尽管2011年取消了相关项目,但希望其再度启用的仍大有人在。从反卫星作战的角度来看,美国最重要的导弹防御能力就是标准三型拦截导弹,这一种导弹被部署在美国海军的各种舰艇上并作为宙斯盾弹道导弹防御系统(BMD)的一部分。2008年,一枚标准三型拦截导弹被用来摧毁脱离运行轨道的一枚失效卫星,美国官员声称,该枚卫星对地面上的人类构成威胁。
前苏联和俄罗斯的反卫星计划: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前苏联就将摧毁对手的空间系统视为可能爆发的全球核战争的一项自然而合理的要求。[42] 为此,他们在技术和资金允许的情况下研发出了无线电电子干扰系统和拦截系统。
前苏联最具影响力的计划就是由导弹发射的陆基共轨“卫星杀手”,其目的旨在摧毁近地轨道的卫星。该系统的主体部队于1967年底正式建立,并于1968年11月1日第一次成功实施了拦截计划。这一系统有能力摧毁飞行高度为250至1000公里(约150到600英里)的卫星,其现场测试于1973年2月在拜科努尔航天发射中心启动。经过进一步的发展(包括其拦截范围的增加),该武器于1978年正式投入使用(指定代号为IS-M)。
1980年4月,前苏联重新启动了这一反卫星系统的测试工作并将其更名为IS-MU。前苏联进行了20多项全面的试验,其中四分之一涉及实体目标。最后的测试是在1982年6月18日进行的。[43] IS-MU的服役时间一直延续到1993年,当时担任俄罗斯总统的鲍里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下令其退役。[44] 这一套复杂的系统旨在对发射后沿轨道公转一圈内的敌方卫星进行拦截,这不利于美国使用地面站进行跟踪,从而便于前苏联开展隐蔽的军事行动。它给美国的KH-11型侦察卫星带来了最大的威胁。[45]
前苏联还针对其他反卫星系统开展了工作。由米格-31截击战斗机携带的“接触”空射型导弹系统与美国的迷你空射型系统类似,前者直到上世纪90年代早期都一直处于研发阶段。不过,在完成测试之前,其研发资金就已全部耗尽。该系统将能够拦截所有在俄罗斯中部上空飞行的近地轨道卫星。
1983年8月,前苏联承诺,不首先在太空部署任何种类的武器,“只要其他国家不在太空部署任何反卫星武器”。[46] 不过,这并不能阻止其最雄心勃勃的研发项目(配备导弹和激光器的Kaskad和Skif在轨反卫星站)的发展趋势。开发上述系统的决定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作出的。反卫星导弹的飞行试验计划在1985年至1986年期间进行,但从未真正付诸实践(可能因为时任前苏联领导人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以政治和经济理由提出了反对意见),并且前苏联从未部署过轨道站。
为了应对“美国战略防御计划“,前苏联于上世纪80年代初重新启动了开发反卫星武器的大规模计划。1985年,所有前苏联的战略开发计划都将重点放在了打击美国的天基弹道导弹防御系统上,包括开发直接攻击这些系统的能力(以及提高攻击导弹的突防能力和发展前苏联类似的天基防御系统)。[47] 前苏联的响应措施包括SK-1000“多功能军事空间系统”计划,其中涉及20多个研发项目,这些项目侧重于空间攻击系统,此外还包括几乎相同数量的天基和陆基的信息支持系统。其中的一个项目就是Naryad-V,其目标旨在开发出由发射井发射型UR-100N和UR-100UTTKh(SS-19)弹道导弹携带的反卫星拦截系统,但该项目在进行飞行试验的过程中被叫停。
在21世纪的前十年,俄罗斯对空间武器的兴趣再度高涨,这主要是因为小布什政府的军事太空计划及其对太空军事化的强硬立场(包括美国拒绝探讨任何限制太空武器的提议)而导致的。鉴于俄罗斯日益隐蔽的常规军事计划和项目,我们只能从独立来源提供的数据来预估其近期开发反卫星武器的行动进展——2009年时任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的弗拉基米尔•波波夫金(Vladimir Popovkin)做的采访是一个重要的例外。[48] 该采访是俄罗斯官方对于这一话题透露的最后一部分公开资料。
波波夫金指出,为了“避免全球政治更加复杂化”,俄罗斯秉承了“乐高”原则,即,俄罗斯正在不断开发并完善反卫星武器的各个独立部分,但只有在出现明确的敌对威胁时,俄罗斯才会将这些部分整合成统一的战斗系统。波波夫金还透露了一些具体项目的细节和进展情况:
- 俄罗斯正在升级其指挥和信息支持系统并计划将其作为开发空天防御系统的一部分(包括购置全新的计算机和信息显示系统)。
- 俄罗斯还致力于提高其空间态势感知能力。俄罗斯正在升级其OS-1和OS-2卫星探测器中心。俄罗斯正在升级其陆基导弹预警站的整体系统,包括以更有效的新型“沃罗涅日”型雷达逐步替换俄罗斯边境沿线以及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地区的陈旧雷达(预警雷达被用于探测和跟踪飞行中的弹道导弹以及追踪航天器的踪迹)。
- 尽管IS-MU反卫星系统于1993年退役,但拜科努尔航天中心保留了这些仍处于正常运行状态的地面指挥计算机和发射平台。
- 虽然与“接触”空射型导反卫星系统有关的工作已经于1995年全面终止,但该系统的所有构成要素(其指挥所、地基Krona卫星识别和瞄准系统、米格-31喷气式飞机和远程导弹)仍在“进一步完善之中”。2012年,第二套Krona系统开始在俄罗斯的远东地区投入运行,以便监测从范登堡空军基地(位于美国西部)发射的卫星。
- 可拦截在地球静止轨道上运行的卫星的IS-MD系统(以IS-MU系统为基础)仍处于开发阶段。该系统的空间跟踪组件之一(位于塔吉克斯坦的Okno系统)现已开始投入使用。该体系可识别静止地球轨道卫星的坐标,同时还可指定计划拦截的目标。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滨海边疆区正在建造第二个系统,以便覆盖从俄罗斯领土上可见的赤道地区上空。
- Naryad-VN和Naryad-VR反卫星系统的储备设施已被封存。
- 阿尔马兹-安泰集团正致力于开发并测试空射型激光器原型,该系统可用于应对美国的侦察卫星以及可探测和跟踪弹道导弹发射情况的预警卫星。
- S-400和S-500防空系统将有望拥有定位近地轨道卫星的能力。
俄罗斯关于交缠的理念及其影响
近年来,俄罗斯的战略思想更加强调将空间作为至关重要的全新军事领域之一,在这一领域内,俄罗斯必须从技术和战略层面发挥影响力。关于这一主题的专业文献花费了很大笔墨来阐述美国的计划及其武器系统的威胁性。例如,2008年,与俄罗斯官方机构具有密切联系的分析人士就曾透露:“美国及其盟国超越北约范围之外的所有[空间]政策无疑都指向一个目标,即,赢得领先于俄罗斯及其他国家的战略军事优势,同时降低后者的核威慑潜力。与其说这是一个趋势,倒不如说它代表了一个基本立场,这与意识形态的分歧并没有任何关系。”[49]
不过,与前苏联时期所不同的是,反卫星武器不仅与全球核战争战略密切相关,同时还与非核冲突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按照俄罗斯的看法,在这种冲突中,美国和北约将拥有极其出色的高精度远程非核武器。不过,这种能力必须依赖于天基指挥、控制、通信和信息资产,而这势必会产生漏洞,俄罗斯必须善加利用这一漏洞。
近年来,俄罗斯的战略思想更加强调将空间作为至关重要的全新军事领域之一,在这一领域内,俄罗斯必须从技术和战略层面发挥影响力。
军事专家的大量专业报告也体现了这一思想。有两位专家曾于2014年坦言,“我们可以肯定,目前已经出现了一个全新的武装冲突领域:航天军事行动战场。这一领域的重要性不断增长,因为它的性质意味着,陆地、海上或空中军事行动的有效性将越来越依赖于使用空间武器的效力及其相关的能力”。[50]
同样,2009年,一名退役中将写道,“空间系统的广泛使用及其对国家现有防御能力日益增加的重要性使其成为极具诱人的目标,破坏这些目标很可能会成为帮助参战一方在武装冲突中赢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从这一方面来看,反卫星系统可以被视为专门用于摧毁另一国的空间信息和情报基础设施资产的工具,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提供集中的军事指挥系统。”[51]
关于俄罗斯军事空间理论的最详细报告来自锦旗设计局的专家们,他们都曾参与反卫星武器的研发过程:
考虑到现代化武器的有效性将越来越依赖于空间要素、现代化多功能空间系统的巨大成本、这些系统在全球经济中的作用和地位及其面对一系列敌对行动时相对缺乏保护的状态,威胁攻击敌方空间系统可以被视为对潜在侵略者的一个额外(在许多情况下,甚至可以说是决定性的)威慑因素。基于可摧毁卫星的武器系统而建立的威慑力量具有明确的优势,从理论上来说,这些优势将有助于在不同层面的冲突中利用上述系统并在避免伤及平民的同时给敌军部队致命一击。……考虑到正在发展中的军事和政治形势、空间军事化及其成为军事行动的主要独立战区之一的总体趋势、由领先国家推动的武器系统的潜在发展趋势及其重点的军事政策以及美国和中国境内的反卫星武器,我们必须及时评估并引入与涉及空间防御(即,应对敌方天基武器的空间防御措施)的一系列问题(包括为这个领域提供融资的优先次序问题)有关的战略决策。[52]
俄罗斯同样担心本国的卫星受到威胁。不过,目前尚不清楚,俄罗斯军事理论的相关政策(即,在“俄罗斯的存亡受到威胁”的前提下允许使用核武器作为应对非核攻击的手段)是否适用于对攻击天基信息和通信系统的行动发起反击的情况。不过,理论和技术的结合确实带来了交缠的风险。
在假设的非核冲突的早期阶段中(俄罗斯将在这些冲突中与美国和北约对峙),哪怕只是在局部或地区性冲突中,地球观测、通信和导航卫星都很可能被视为无线电电子干扰或实体攻击的合理目标。最有可能的目标就是近地轨道上的侦察卫星。如果对手部署了拥有必要技术特征的反卫星武器,那么运行在更高轨道上的卫星也将面临危险。这将包括在中地球轨道上运行的导航卫星、俄罗斯现有的格洛纳斯系统(宇宙系列)以及美国的NAVSTAR卫星群(该卫星群可以提供全球定位系统信号)。在地球静止轨道和高椭圆轨道上运行的通信卫星(包括美国的MILSTAR卫星和先进极高频卫星群以及俄罗斯的“子午线”卫星、RADUGA和未来的Sfera-V系列)也将变得岌岌可危。[53] 事实上,在2009年接受采访时,波波夫金就曾表示,Naryad-VN和Naryad-VR反卫星系统能够涵盖地球静止轨道及其他类型的高轨道,这意味着,它们可以对美国的这些军用卫星构成威胁。
部分此类卫星同时为美国和俄罗斯的战略核系统服务,从而产生了交缠问题。因此,破坏这些卫星将有可能使冲突立即升级为核战争,特别是由于战略部队可能一直处于高度戒备的状态(即使在局部武装冲突的情况下亦是如此)。通信卫星对于指挥和控制海上导弹潜艇和执行巡逻任务的轰炸机具有异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危机或局部战争中,大量潜艇和飞机将被调动起来。
从交缠的角度来看,针对导弹预警卫星发动的攻击可能更具危险性。这种卫星通常都位于地球静止轨道或高椭圆轨道上。目前,俄罗斯只拥有两枚全新的苔原轨道级预警卫星,但根据其2020年至2025年间的国家军备计划,俄将部署更多的这一类卫星并将其作为用于军事指挥和威胁探测的统一空间系统的一部分。[54] 同时,美国也以全新的天基红外系统(SBIRS)卫星替换了陈旧的国防支援计划卫星。
有限战略打击的逻辑(尽管这一逻辑仍值得推敲)指出,应保留双方的预警卫星,以便尽可能限制所有核交锋的规模。
在非核战争期间,这些卫星可能不会受到反卫星作战行动的影响。不过,由于俄罗斯空天军事战略缺乏透明度,这将导致全球非核战争和核战争之间的界线模糊不清,因此,我们很难确定导弹预警卫星的免疫力。为了达到预期的效果,特定的核武器或常规战略打击需要突破对手有限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这可能就需要摧毁在地球静止轨道上运行的预警卫星以及远程陆基和海基雷达。
由于俄罗斯的洲际弹道导弹已经为“基于预警发射”或“遇袭即发射”的状态作好了准备,因此,摧毁预警卫星可能会被视为发动攻击及促使俄罗斯政府启动导弹发射程序的前兆因素——虽然在标准程序中,在实际发射前首先需要通过陆基预警雷达或上述雷达被破坏的事实来确定遇袭的情况。如果沿俄罗斯边境线的陆基雷达同时或提前遭遇到袭击,那么相应的风险将更大。俄罗斯政府认为,美国充分了解攻击俄罗斯这一类卫星将导致的所有后果,而当本国的导弹预警卫星遭遇到类似的攻击时,美国也将以同样的方式以牙还牙。有限战略打击的逻辑(尽管这一逻辑仍值得推敲)指出,应保留双方的预警卫星,以便尽可能限制所有核交锋的规模。不过,由于军民两用通信卫星(这一类卫星同样被部署在地球静止轨道上)被反卫星战争理论视为合理的目标,因此,即使是在局部或地区性的常规冲突中,一部分预警卫星仍有很高的概率意外遭袭,从而导致随之而来的后果。这种相互作用构成了另一种形式的交缠,并成为反对选择性或量体裁衣式战略核方案(这些方案模糊了常规战争和核战争之间的界线,同时也降低了核武器的使用门槛)这一高风险概念的有力证据。
陆基雷达将很难探测或跟踪高超音速助推滑翔武器,如果部署上述武器,那么针对预警卫星的打击就将变得极其危险。事实上,在破坏对手的天基导弹预警系统后,太空系统将无法“侦查到”利用高超音速武器发动的攻击。
总的来说,俄罗斯政府很可能认为,针对预警卫星的攻击比针对天基通信系统的攻击更加危险。俄罗斯对通信卫星的依赖程度远远低于美国,因为其最可能组织军事行动的战区通常都与其领土直接相邻或近在咫尺,而其地面部队(而非其空军和海军部队)更有可能在这些战区的作战行动中发挥主要作用(俄罗斯在叙利亚的作战行动自然是这一模式的例外情况,但上述行动从未被视为针对美国或其主要盟国的军事行动)。与此同时,由于俄罗斯的主要战略部队都包含配备多个分导式再入飞行器的发射井式洲际弹道导弹(包括陈旧的和未来的重型导弹),所以,与美国相比,俄罗斯政府自然会更谨慎地避免这些导弹遭到破坏。因此推测,俄罗斯对“基于预警发射”或“遇袭即发射”模式的依赖程度远高于美国。如果没有预警卫星提供最早的警报信号来启动发射导弹的命令程序并由陆基雷达确认攻击行动,那么这样的战略就只是纸上谈兵。
结论
美国和俄罗斯的政治领导人应该了解交缠的危险,并为上文所提及的情境作好准备。他们需要了解新武器对稳定的破坏性作用及与之相关的作战概念(这些概念将导致交缠威胁,甚至可能导致全球各国陷入无可回避的灾难之中)。除了战略和专业技术以外,避免这种威胁将需要巨大的政治意愿和外交努力。但目前几乎看不到这种努力。
美国和俄罗斯的政治领导人应该了解交缠的危险。
如果能够恢复双边战略武器管制的话,我们就可以据此降低助推滑翔系统的风险。《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New START)的后续协议所规定的关于投射发射载具和弹头的重要原则可以适用于洲际助推滑翔系统(例如第二代高超音速飞行器、先进高超音速武器和4202专案),无论相关系统是否配备了常规弹头或核弹头。以这种方式限制其数量将有助于缓解俄罗斯的担忧(俄政府担心这些系统将被用于常规攻击之中,这些攻击可能危及该国的军事安全、甚至可能在和平时期从政治层面上贬低其核武器的潜力,而上述潜力正是曾作为超级大国的俄罗斯目前仅存的优势之一)。我们应该通过拓展1987年签署的《中远程核力量条约》的相关规定来禁止陆基中程或远程助推滑翔系统的使用。
我们或许可以通过建立互信和提高透明度的协议对海上发射或空射型常规巡航导弹所带来的真实或假设的打击军事目标威胁进行管理,上述协议将禁止在双方战略目标范围内秘密集结海军和空军部队。根据这些协议,如果没有事先通知及可信的善意解释,那么将美国的飞机和水面舰艇重新部署至前线据点以及从港口派遣比常规行动更多的巡航导弹潜艇将令俄罗斯拉响警报。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政府的进攻和防御部队将进入高度戒备的状态,以便降低对手突袭成功的可能性。
如果俄罗斯能够通过这一类协议来缓解其对助推滑翔武器和常规巡航导弹的担忧,那么俄罗斯的空天部队就可以将其重点从空天战争概念转向第三方国家、流氓政权和恐怖分子针对城市工业中心发动的有限核空袭和导弹袭击导致的现实威胁。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和俄罗斯合作开发和运行防御系统的计划将再次变得可行。
就反卫星武器的交缠风险而言,唯一的好消息是,目前美国和俄罗斯均未部署专门的反卫星作战武器。目前仅有两用系统(例如:美国的标准三型拦击导弹和陆基拦截系统以及俄罗斯的S-400和未来的S-500空中和导弹防御系统)拥有反卫星能力。其他的反卫星功能已被禁用,或仍处于不同的研发阶段。这为“如何对专用反卫星武器的试验和部署工作进行现实可行的限制”预留了谈判的空间。关键的天基核指挥、控制、通信和信息卫星(特别是预警和通信卫星)通常都在地球静止轨道或高椭圆轨道上运行,只有专门的反卫星系统才有可能对其构成威胁(两用的空中和导弹防御系统无法企及这一类轨道)。因此,为了减少交缠所产生的部分高风险问题,确保卫星安全(这些卫星对核指挥、控制、通信和信息系统至为关键)的协议(即使这一类协议无法减少两用空中或导弹防御系统所带来的反卫星威胁)仍将大有裨益。
注释
[1]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战争浅析》,由迈克尔·霍华德(Michael Howard)和彼得·帕雷特(Peter Paret)编辑和翻译(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6年),第87页。
[2] 俄罗斯于2016年发布的官方文件《俄罗斯外交政策的概念》是少有的例外之一,该文件提到了相关的可能性,信息来源:http://www.mid.ru/foreign_policy/news/-/asset_publisher/cKNonkJE02Bw/content/id/2542248。
[3] 《Vozdushno-kosmicheskie sily RF pristupili k sluzhbe》(《俄罗斯联邦开始启用空天部队》),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2015年8月3日,http://www.interfax.ru/russia/457604;以及《Vozdushno-kosmicheskie sily》(《空天部队》),俄罗斯联邦国防部,信息获取时间:2017年10月13日,http://structure.mil.ru/structure/forces/vks.htm。
[4] 《Voennaya doktrina Rossiiskoi Federatsii》(《俄罗斯联邦的军事理论》),俄罗斯总统,2014年,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47334。
[5] 安德烈·德民(Andrei Demin)等人,《Sereznoi ugroze adekvatnyi otvet。Osnovnoi sferoi vooruzhennoi borby stanet vozdushno-kosmicheskoe prostranstva》(对严重威胁的恰当响应。空天战场将成为武装冲突的主要地区),《航空防御》,2012年8月13日,http://www.vko.ru/strategiya/sereznoy-ugroze-adekvatnyy-otvet。
[6] 尤里·克里尼特斯基(Yury Krinitsky),《Nauchno-kontseptualnyi podkhod k organizatsii VKO Rossii》(《俄罗斯空天防御体系的科学和概念化方法
》),《航空防御》,2013年2月19日,http://www.vko.ru/koncepcii/nauchno-konceptualnyy-podhod-k-organizacii-vko-rossii。
[7] 同上。
[8] 维亚切斯拉夫·巴斯卡阔夫(Vyacheslav Baskakov),《Kosmicheskie Voiska kak garantiya oborony strany》(《航天部队是国家防御体系的保障》),Nezavisimoe voennoe obozrenie,2004年10月1日,http://nvo.ng.ru/concepts/2004-10-01/4_cosmos.html。
[9] 德民等人,《Sereznoi ugroze adekvatnyi otvet》。
[10] 《Kazhdyi pyatyi rubl-na VKO》(《空天防御在国防经费中所占的比重为五分之一》),Voenno-promyshlennyi kurer,2012年2月21日,http://vpk-news.ru/news/403。
[11] 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更大更强:对俄罗斯国家安全的保证》,俄罗斯联邦总理办公室官方网站的档案(2008年-2012年),2012年2月20日,http://archive.premier.gov.ru/eng/events/news/18185/。
[12] 阿列克谢·阿尔巴托夫(Alexei Arbatov),《Sovmestnaya PRO nikak ne poluchaetsya》(《联合导弹防御系统将无法发挥作用》),Nezavisimoe voennoe obozrenie,2011年6月17日,http://nvo.ng.ru/concepts/2011-06-17/1_pro.html。
[13] 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1984年1月25日美国国会联席会议前关于国情咨文的讲话》,《美国总统计划》,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pid=40205。
[14] 克里尼特斯基,《Nauchno-kontseptualnyi podkhod k organizatsii VKO Rossii》。
[15] 维克托·米亚斯尼科夫(Viktor Myasnikov),《Protivoraketnaya i protivovozdushnaya oborona Rossii budet luchshei v mire》(《俄罗斯计划建立全球最先进的空中和导弹防御系统》),Nezavisimoe voennoe obozrenie,2014年12月12日,http://nvo.ng.ru/armament/2014-12-12/1_oborona.html。
[16] (Oleg Grinevskyi),Perelom。《Ot Brezhneva k Gorbachevu 》(《勃列日涅夫背离戈尔巴乔夫》)(莫斯科:奥尔玛出版社,2004年),69页-75页。
[17] 同上。
[18] 《Proizvodstvo ballisticheskikh raket otstaet ot grafika》《(弹道导弹的生产进度滞后)》,Nezavisimoye voennoe obozrenie,2017年1月27日,nvo.ng.ru/armament/2017-01-27/2_934_red.html。
[19] 谢尔盖·苏克哈诺夫(Sergei Sukhanov),《VKO eto zadacha, a ne sistema》(《空天防御是一项任务,而不是一个系统》),《航空防御》,2010年3月29日,http://www.vko.ru/koncepcii/vko-eto-zadacha-ne-sistema。
[20] 《V Sovfede poobeshchali voennyi otvet na razmeshchenie PRO SShA v Rumynii i Polshe》(《俄罗斯联邦委员会承诺将对美国部署在罗马尼亚和波兰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采取军事对策》),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2016年5月12日,http://www.interfax.ru/russia/507970。
[21] 《Aktualnye zadachi razvitiya Vooruzhennykh Sil Rossiiskoi Federatsii 》(《俄罗斯联邦发展武装部队的关键任务》)(莫斯科:俄罗斯国防部,2003年);康斯坦丁·希夫科夫(Konstantin Sivkov),《Pravo na udar》(《攻击的权利》),Voenno-promyshlennyi kurer,2014年3月5日,http://vpk-news.ru/articles/19370;马克尔·伯伊索夫(Markell Boytsov),《Terminologiya v voennoi doctrine》(《军事理论术语》),Nezavisimoe voennoe obozrenie,2014年10月31日,http://nvo.ng.ru/concepts/2014-10-31/10_doctrina.html;戴维·列尔曼(David Lerman)和特里·阿特拉斯(Terry Atlas),《美国称,俄罗斯的“武力恫吓”对稳定造成了威胁》,彭博社,2015年6月25日,http://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5-06-25/russia-s-nuclear-saber-rattling-threatens-stability-u-s-says。
[22] 《Voennaya doktrina Rossiiskoi Federatsii》。
[23] 德米特里·阿克莫洛夫(Dmitry Akhmerov)、叶甫根尼·阿克莫洛夫(Yevgeny Akhmerov)和马拉特·瓦列耶夫(Marat Valeev),《Aerostat-drug “Sarmata”》(《轻航空器--“萨尔玛特”导弹的好帮手》),Voenno-promyshlennyi kurer,2016年10月12日,http://vpk-news.ru/articles/32887。
[24] 达里尔·G·金博尔(Daryl G. Kimball),《第三次世界大战在即?进入未知领域后,特朗普使用核武器的权利:“迎战军备竞赛。我们将取得胜利,并将打败他们所有人……”》,《全球研究》,2017年2月4日,http://www.globalresearch.ca/world-war-iii-trumps-authority-to-use-nuclear-weapons-let-it-be-an-arms-race-we-will-outmatch-themand-outlast-them-all/5572887;罗伯特·莱格沃尔德(Robert Legvold),《新核时代在21世纪全球(混乱)秩序中的挑战》,《多极世界核中的挑战与机遇》,由阿列克谢·阿尔巴托夫(Alexei Arbatov)和弗拉基米尔·德沃尔金(Vladimir Dvorkin)编辑,(莫斯科: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即将出版);以及约翰·M·唐纳利(John M. Donnelly),《美国国防部敦促特朗普团队增加核方案》,《清单》,2017年2月2日,http://www.rollcall.com/news/policy/pentagon-panel-urges-trump-team-expand-nuclear-options。
[25] 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大会》,俄罗斯总统办公室,2015年10月22日,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50548。
[26] 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大会》,俄罗斯总统办公室,2014年10月24日,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46860。
[27] 《Tekst vystupleniya Dmitriya Rogozina na press-konferentsii v “RG”》(《德米特里·罗戈津在RG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Rossiiskaya gazeta,2013年6月28日,https://rg.ru/2013/06/28/doklad.html。
[28] 米亚斯尼科夫(Myasnikov),《Protivoraketnaya i protivovozdushnaya oborona Rossii budet luchshei v mire》。
[29] 尤金·米亚斯尼科夫(Eugene Miasnikov),《对俄罗斯的航空航天威胁》,《导弹防御中的对抗与合作》,由阿列克谢·阿尔巴托夫(Alexei Arbatov)、弗拉基米尔·德沃尔金(Vladimir Dvorkin)和纳塔莉亚·巴布诺娃(Natalia Bubnova)编辑(莫斯科: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2013年),121页-146页。
[30] 《Sergei Shoigu:za tri goda Rossiya uvelichit kolichestvo krylatykh raket v pyat raz》(《谢尔盖·绍伊古:俄罗斯将在三年内将巡航导弹的数量增加五倍》),TASS,2013年7月5日,http://tass.ru/arhiv/629786。
[31] 《Voennaya doktrina Rossiiskoi Federatsii》。
[32] 亚历山大·瑞格罗德茨基(Alexander Raigorodetsky),《Proekt MBR “Albatros” (SSSR)》(《“信天翁”洲际弹道导弹项目(前苏联)》),《战祸》,2011年8月15日,http://www.dogswar.ru/oryjeinaia-ekzotika/raketnoe-oryjie/4945-proekt-mbr-qalbatros.html;阿列克谢·拉姆(Alexey Ramm)和德米特里·科尔内夫(Dmitry Korneev),《Albatros’ mirovoi revolyutsii, chast’ 1 》(《引发全球革命的“信天翁”,第一部分》),Voenno-promyshlennyi kurer,2015年9月23日,http://www.vpk-news.ru/articles/27160;阿列克谢·拉姆(Alexey Ramm)和德米特里·科尔内夫(Dmitry Korneev),《Gipersmert na podkhode》(《超级死神来袭》),Voenno-promyshlennyi kurer,2015年3月25日,http://www.vpk-news.ru/articles/24407。
[33] 瑞格罗德茨基,《“信天翁”洲际弹道导弹项目(前苏联)》
[34] 《Proizvodstvo ballisticheskikh raket otstaet ot grafika》。
[35] 《Voennaya doktrina Rossiiskoi Federatsii》
[36] 拉姆(Ramm)和科尔内夫(Korneev),《Gipersmert na podkhode》。
[37] 德米特里·阿克莫洛夫(Dmitry Akhmerov)、叶甫根尼·阿克莫洛夫(Yevgeny Akhmerov)和马拉特·瓦列耶夫(Marat Valeev),《Po-bystromu ne poluchitsya》(《并非迫在眉睫》),Voenno-promyshlennyi kurer,2015年10月21日,http://vpk-news.ru/articles/27617。
[38] 詹姆斯·M·阿克顿(James M. Acton),《是否万全之策?就常规“快速全球打击”提出准确的问题》(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2013年),33页-63页。
[39] 主要作战局副局长维克托·坡茨尼希尔(Victor Poznihir)中尉在第六届莫斯科国际安全大会上的简报,2017年4月26日-27日。
[40] 艾玛·勒克斯顿(Emma Luxton),《哪些国家用于太空探索的经费是最多的?》,世界经济论坛,2016年1月11日,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16/01/which-countries-spend-the-most-on-space-exploration/。
[41] 鲍里斯·莫尔查诺夫(Boris Molchanov),《航空航天武器的军事化》,《核扩散:新技术、武器和条约》,由阿列克谢·阿尔巴托夫(Alexei Arbatov)和弗拉基米尔·德沃尔金(Vladimir Dvorkin)编辑(莫斯科: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2009年),160页-185页。
[42] 弗拉基米尔·德沃尔金(Vladimir Dvorkin),《航天武器计划》,《外太空:武器、外交和安全》,由阿列克谢·阿尔巴托夫(Alexei Arbatov)和弗拉基米尔·德沃尔金(Vladimir Dvorkin)编辑,(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2010年),30页-45页。
[43] 莫尔查诺夫,《航空航天武器的军事化》;以及马克西姆·塔拉森科《Voennye aspekty sovetskoi kosmonavtiki 》(《前苏联的军事太空探索》)(莫斯科:TOO Nikol;Agentstvo Rossiiskoi pechati,1992年)。
[44] 由谢尔盖·伊万诺夫(Sergei Ivanov)编辑,《Entsiklopediya 21 vek. oruzhie i tekhnologii Rossii 》(《21世纪百科全书:俄罗斯的武器和技术》),第5卷,《Kosmicheskie sredstva vooruzheniya》(《航天武器》)(莫斯科:武器与技术出版社,2002年)。
[45] 《Rossiya razrabatyvaet protivosputnikovoe oruzhie v otvet na shagi SShA v etoi sfere, zayavil v chetverg zhurnalistam v Moskve zamestitel ministra oborony RF po vooruzheniyu general armii Vladimir Popovkin》(《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弗拉基米尔·波波夫金于周四向记者透露,俄罗斯正针对美国在空天领域内的举措开发反卫星武器》),俄罗斯新闻社,2009年3月5日;以及亚历山大·克罗希金(Alexander Khoroshikh),《Re:Protivokosmicheskaya oborona》(《回复:反空间防御》),航天论坛,2009年12月13日,http://www.astronomy.ru/forum/index.php/topic,69231.msg1108417.html#msg1108417)。
[46] S·V·查卡斯(S. V. Cherkas),Sovremennye politiko-pravovye problemy voenno-kosmicheskoi deyatelnosti i osnovy metodologii ikh issledovaniya》(《当代军事太空活动的政治和法律问题及基本研究方法》)(莫斯科:MO,1995年)。
[47] 帕维尔·波德维格(Pavel Podvig),《似是而非的漏洞:前苏联在上世纪70年代的军事建设--研究纪要》,《国际安全》第33期,第1号(2008年):118页-138页。
[48] 《Rossiya razrabatyvaet protivosputnikovoe oruzhie v otvet na shagi SShA v etoi sfere》。
[49] 谢尔盖·苏克哈诺夫(Sergei Sukhanov)、弗拉基米尔·格林柯(Vladimir Grinko)和弗拉迪米尔·斯米尔诺夫(Vladimir Smirnov),《Kosmos v voprosakh vooruzhennoi borby》(《太空武装冲突的问题》),Natsionalnaya oborona,第7号(2008年7月):41页。
[50] 瓦西里·多尔戈夫(Vasiliy Dolgov)和尤里·坡德戈尔尼克(Yury Podgornykh),《Gospodstvo v kosmose-pobeda na zemle》(《太空优势,地球霸主》,空天防卫部队,2014年6月8日,http://www.vko.ru/strategiya/gospodstvo-v-kosmose-pobeda-na-zemle。
[51] 叶夫根尼·布钦斯基(Evgeny Buzhinsky),《Kosmos: Novyi TVD ili sfera sotrudnichestva》(《太空:究竟是新战场还是合作领域?》),Nezavisimoe voennoe obozrenie,2009年4月10日,http://nvo.ng.ru/armament/2009-04-10/1_space.html。
[52] 苏克哈诺夫、格林柯和斯米尔诺夫,《Kosmos v voprosakh vooruzhennoi borby》:第42页。
[53] 阿纳托利·扎克(Anatoly Zak),《军用卫星的恐怖世界》,《俄罗斯太空网》,2016年12月17日,http://www.russianspaceweb.com/spacecraft_military.html。
[54] 瓦西里·米亚斯尼科夫(Vasily Myasnikov),《Edinaya kosmicheskaya sistema predupredit o yadernom napadenii》(《统一的空间系统将针对核攻击发出警报》),Nezavisimoe voennoe obozrenie,2014年10月17日,http://nvo.ng.ru/armament/2014-10-17/1_shojgu.html;以及塔吉亚娜·格瑞纳(Tatyana Gorina),《Rossiya ostalas bez ‘Oka’:kogda zarabotaet novaya kosmicheskaya sistema preduprezhdeniya o raketnoi atake? 》(《俄罗斯没有“奥卡”:全新的航天导弹袭击警报系统将从何时开始投入使用?》),《莫斯科共青团报》,2015年2月11日,http://www.mk.ru/politics/2015/02/11/rossiya-ostalas-bez-oka-kogda-zarabotaet-novaya-sistema-obnaruzheniya-raket.html。
关于作者
阿列克谢·阿尔巴托夫 NAME_MISSING
弗拉基米尔·德沃尔金 NAME_MISSING
彼得·托皮契卡诺夫 NAME_MISSING
简介
军事技术的两大发展让核领域不再孤立。首先,大量新兴非核技术可以与核武器及其指挥、控制、通信和信息(C3I)系统相互作用,包括高超音速、反太空、网络、无人自动武器、精确制导武器和导弹防御技术。其次,多功能军事技术越来越常见,既可以用于常规作战也可以用于核作战,亦可同时威胁潜在敌人的核资产和常规资产。
非核技术和核技术的交缠,对于常规战争升级到核战争有着重要影响。虽然美国学者已经开始研究升级风险,但对中国如何看待此问题尚无系统性的了解。然而,交缠问题又的确与中国有关。美国先进非核武器可以威胁到中国的核力量及其C3I基础设施。中国一直密切关注美国及俄罗斯的非核技术开发工作,同时,其自身也有类似开发项目。这些武器一旦部署,也可威胁美国核C3I基础设施。
在此背景下,本章集中讨论交缠导致非核冲突上升为核冲突的四种可能途径。第一,某些武器和军事资产可能因其多种用途引起误解而导致意外升级。多功能打击武器和多功能打击目标(包括武器或其支持系统)都会引起误解。
非核技术和核技术的交缠,对于常规战争升级到核战争有着重要影响。
第二,对部署特定武器的目的和影响、或该武器将于何种情况下被使用可能引起战略误解和误判。比如,美国和中国对于彼此在何种情况下会使用反卫星(ASAT)武器有着不同理解,两国对美在韩部署末段高空区域防御(萨德,THAAD)系统背后的目的和影响也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这些分歧可能在危机期间引发意外升级。
第三,某些非核技术的开发和部署可能影响一国在危机期间承受风险的倾向,从而增加或减少主动升级的可能性。第四,某些非核技术的引进可能减轻、也可能加重战争迷雾(即感知战争态势时不可避免的不确定性),从而影响意外核升级的风险。
本章将介绍并阐释中国学者对于交缠经由四种途径引发升级风险的看法,并与西方学者的观点作对比,同时介绍作者本人对升级风险的看法。另外,本章探讨了中国是否真如一些西方学者所说,故意利用交缠引起的升级风险增强威慑力。中国对美国常规精准打击武器和导弹防御影响其核威慑力的担忧是严肃且众所周知的,本文因此没有对此再进行详述。
为了解中国对各升级途径的看法,作者全面梳理了现有公开文献,进行了大量访谈,并与来自军界、外交政策界、国防科技工业、智库、学术界的中国资深专家举行了闭门圆桌会议。交流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中方专家观点并非大统一。因此,本章侧重阐释中方主要观点,同时也介绍一些国际学界可能感兴趣的少数派观点。
中国关于升级的思想
意外升级一直不是中国安全思想的重点。[1]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没有深入涉及意外升级或危机管理。毛泽东带领中国革命期间,中国安全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也强调通过不确定性迷惑敌人的战术,其目的是让敌人无法准确知晓中国自身能力和真实目标,同时尽可能了解敌人的能力和意图。[2]这一传统思想与西方常见的思想学派有较大差异,后者主张让对手正确评估自己的意图和能力,有助于避免意外升级。
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获得核武器能力之后,除了1969年的中苏边界危机(据称当时苏联暗示要对中国基本核能力展开外科手术式打击)外,几乎没有卷入重大国际核危机的切身经历。
中国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倾向于认为,只在有绝对把握(或接近绝对把握)取得胜利的情况下,才应当采取军事行动。毛泽东强调的三大作战原则中,有一个涉及使用军事力量的条件:“作战的致胜原则就是:要么不打,要打就要打赢。坚决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3]受该原则影响,中国战略家倾向于不过多考虑胜利或失败之外的其它情况。此原则也反映出中国长期以来相信最高决策者可以较充分地掌控战争的具体进程,从而没有过多考虑战争进程可能涉及的诸多不确定因素,尤其是最高决策者可能并不能完全实时了解战场态势、或者不能有效管控具体军事行动的风险。
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获得核武器能力之后,除了1969年的中苏边界危机(据称当时苏联暗示要对中国基本核能力展开外科手术式打击)外,几乎没有卷入重大国际核危机的切身经历。[4]相反,美国和苏联直接经历了大量严重核危机,包括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美苏从中切实感受到冲突意外升级的巨大风险,进而在后期进行了一系列合作,通过签订双边防止核战争协定以及建立降低核风险中心等方式降低意外升级的危险。相比之下,中国没有严重的核危机经历,因此对意外升级的风险没有第一手体验。
数十年来,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加深,国内战略学界与西方交流愈加频繁,中国的思想也在演进和发展。
20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更加关注国际危机如何更可能起源于国内因素而非国际紧张局势。[5]此外,中国传统观点认为公开讨论升级风险或危机管理本身会传递出软弱信号,[6]而决不向敌人妥协既是一项神圣原则,也被认为是决策者基本素质的重要体现。这种观点进一步降低了中国专家研究如何避免或减缓升级风险的兴趣。
数十年来,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加深,国内战略学界与西方交流愈加频繁,中国的思想也在演进和发展。中国专家逐渐了解并接受了部分西方文献概念,包括升级和危机稳定。国内关于升级的讨论也日益频繁,越来越多的中国专家开始分析战略安全问题对军备控制稳定性和危机稳定性的影响。此发展趋势反过来也促进了中国与西方战略学界的深入交流。[7]
即便如此,传统观点和看法仍然或多或少地影响着中国对这些问题的总体理解。传统中国观点和西方思想的不断碰撞和融合,使得中国当前对交缠与意外升级之间的关系形成了复杂的看法,十分值得探讨。
多功能装备引发误解
多功能目标
有的武器装备或其支持系统既能在常规军事行动中发挥作用,也能在核军事行动中发挥作用。在一场常规冲突中,如果此类多功能资产受到袭击,受袭国家可能难以正确解读敌人的潜在意图,因为敌人的袭击目的既可能是破坏己方的常规军事行动能力,也可能是破坏己方的核力量使用能力,而后者必然引发己方更大的担忧。受袭国家如果认为其核力量受到直接威胁,有可能考虑启动严厉的报复措施,包括进行核反击准备。
举例而言,美国预警卫星能够提供核洲际导弹攻击的战略预警,同时也能加强美国区域导弹防御能力(比如对敌方的中程常规导弹提供预警数据)。美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保护范围一定程度上取决于预警时间:发出警报的时间越早,保护区越大。[8]发生导弹袭击时,美国预警卫星发出的警报一般早于地面雷达,因此可以提高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战斗能力。美国曾表示,担心中国可能将美预警卫星作为打击目标。2016年美国国防部呈交国会的年度报告《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和安全发展》便提到了这一担忧。[9]美国学者还举出中国人民解放军(PLA)空军出版物的观点:“在与美军的海上交锋中,击落美国预警卫星可以避免升级、稳定事态。”[10]美国高层官员曾公开提及此类报告。[11]
确实有中国专家指出,如果中美两国在台湾海峡打响常规战,中国应当考虑摧毁美国预警卫星,削弱美国的战区导弹防御能力,从而确保中国常规导弹可以有效打击美军和/或台湾目标。[12]对美方而言,考虑到预警卫星对美国战略核指挥、控制和通信系统的重要性,中国打击预警卫星可能被理解成中国有意破坏美国侦测和拦截洲际弹道导弹的能力,并被美国误认为是中国意欲向美国国土发射洲际弹道导弹(ICBM)的先兆。美国由于担心中国打击预警卫星可能预示着中国即将向美国发射洲际弹道导弹,从而可能抢先对中国的战略核力量发动先发制人打击。如此一来,对多功能军事资产进行打击——比如本例中的美国预警卫星——便可能引起意外升级。
同样,美国战略界一直担忧中国没有专用的核指挥控制系统、担忧中国部分军用通讯系统既要支持核军事行动,又要支持常规军事行动。[13]中国的情况是否确实如此,很难根据公开信息进行确认。由于对专用的核指挥控制系统缺乏明确的定义,即便中方专家对此也无一致看法。国外专家的担忧包括,中国的东风-21、东风-26等弹道导弹据称有核型号,又有常规弹头型号,美国可能在常规战争中把中方的核导弹误认成常规导弹进行打击,从而带来意外升级的风险。此外,美方专家认为中国一些导弹基地同时部署核导弹和常规导弹,或许还“共用支持力量和设施”。[14]核导弹和常规导弹共用基地或设施的做法被认为是可能引发意外升级的又一因素。
迄今,中国分析人士对多功能装备以及核常混合部署可能引起的升级风险,与西方专家的看法存有较大差异。中国大部分政策界和技术界专家,并没有专门考虑多功能装备及核常混合的战争升级风险,在制定和审议政策时较少将其考虑在内。[15]事实上,中国文献几乎极少谈及相关的升级风险。
有关文献的缺乏可以部分归因于中国核事务保密级别相对较高。某种程度上,中国政府内的安全和军事专家仍然受传统体制的影响,机构和部门之间的沟通程度并不高。获准参加国际交流和对话的很多中国专家,可能并不清楚中国核力量的具体安排,也不完全熟悉关于核常混合的具体政策问题。在二轨对话会中,美方经常会就一些具体的政策问题提问,比如,如果美国针对中国常规能力发动常规打击却意外破坏到中国核能力时,中国可能如何反应?在回答这类问题时,中方参会者的观点似乎只是推测,而不是基于对己方具体政策的确凿了解。如此局面增加了开展实质性讨论并达成共识的难度。
中国专家和国外专家对特定军事行动的目的和影响的不同看法,也可能无意中带来升级风险。例如,从中国的角度看,中美如果在台湾海峡打响常规战,中国打击美国预警卫星显然只是战术军事行动,其目的仅仅是破坏美国的战区导弹防御能力。虽然一些中国专家明白美国的预警卫星也为核大战提供战略预警,但他们似乎认为美国肯定能够正确理解中国在常规、有限、局部战争中使用反卫星武器的意图。他们的理由是中国并没有能力威胁美国的大规模核力量,所以美国应该明白中国即使破坏了美国战略预警能力也无法借此对美国进行先发制人的核打击而不遭受核报复,所以破坏美国的战略核能力不可能是中方使用反卫星武器的意图。但在很多美方专家眼里,中国可能对美国小规模地首先使用核武器,以便对美国进行恐吓、而非试图先发制人地解除美国的核武装;因此,美国认为中国攻击美国预警卫星确实可能是对美使用核武器的先兆。
换句话说,美国官员和专家对于此类打击的目的和影响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他们普遍认为打击预警卫星是对美国核武器C3I系统的严重威胁,因此极具挑衅意味,美国应该考虑强硬回击。[16]双方认知的这种差异可能引发误判和意外升级。
中西方战略家的思维差异有助于解释双方对中国核态势的不同解读。有国外分析人士提出,中国可能故意将核能力和常规军事能力混合,以此保护其常规导弹不被敌人攻击。[17]他们认为中国的想法是:在范围有限的常规冲突中,由于中国常规力量部署地非常靠近核力量,使得误击核力量的风险太高,敌人会因此避免攻击中国的常规力量。
事实上,中国战略家没有太多考虑混合部署对升级风险的影响,这从侧面说明中国不是为了保护常规力量而采取混合部署。
然而,实际上并没有确凿证据表明中国因此故意混合部署核力量和常规力量,也没有迹象表明中国以后会这样做。事实上,中国战略家没有太多考虑混合部署对升级风险的影响,这从侧面说明中国不是为了保护常规力量而采取混合部署。此外,中国专家似乎不接受用核力量保护常规力量这一逻辑。相反,他们认为核力量的生存比常规力量重要得多。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军事规划者试图用核力量保护常规力量的猜测并不符合事实。[18]
事实上,中国核与非核混合部署主要受工程和后勤便利因素推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专家最近提到,新公开的东风-26中程弹道导弹使用核弹头和常规弹头,且可以根据战场具体需求,迅速在核弹头与常规弹头之间进行转换。他们认为,由于中国的核武库规模很小,使得核导弹具备发射常规弹头的能力可以提升中国应对“多元安全威胁”的效果。[19]中国常规力量和核力量的混合部署似乎也是出于类似原因。
多功能打击武器
部署或使用可同时威胁核目标和常规军事目标的进攻性武器,同样会引起误解。很多新型非核武器威胁到的目标范围非常广泛。比如,常规高超音速武器的潜在目标包括重要恐怖分子、雷达、反卫星武器、核导弹和常规导弹的运输起竖发射车(TEL)。此外,高超音速武器具有飞行中的机动性,造成目标点的不确定性——即目的地不明确。因此,假如中国探测到美国向中国方向发射高超音速武器,那么武器落地前中国无法知晓打击目标是在朝鲜、俄罗斯东部还是中国。即便在武器行程后期可以确定打击目标是中国,中国仍然不能肯定美国是要攻击人口中心、军事指挥控制设施、导弹基地、战备机动中的核导弹发射车还是反卫星武器发射装置,同时也很难确定来袭武器安装了常规弹头还是核弹头——即弹头不明确。由于目的地和弹头不明确,加之该武器兼具摧毁核目标和常规目标的能力,这会引起误判和重大升级风险。[20]
中国专家似乎不太关注上述的不确定性以及相关的升级风险。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长期以来就认为美国有使用高超音速武器对中国核力量进行先发制人打击的意图。即便高超音速武器只能携带常规弹头,中国分析人士仍担心其高速和高精确度完全可以使其用于先发制人打击。[21]2002年美国核态势评估将“非核攻击能力”纳入新三位一体(旨在发展核与非核打击能力、战略防御和灵活反应的基础设施),[22]同时美国全球快速常规打击项目(旨在开发远程高超音速非核武器)不断取得技术突破,中国的担忧也逐渐增加。因此,有两个原因使得中国可能将某些来袭的高超音速武器解读为旨在打击中国的核力量:一是中国认为美政府开发高超音速武器本来就是针对中国的核力量,二是中国尚未对来袭弹头和目的地的不确定性可能引起的误解风险进行全面研究。
无人潜航器(UUV)是可能因其多功能引起意外升级的新兴非核能力的又一个例子。有些攻击性的无人潜航器既可以威胁敌人的弹道导弹核潜艇(SSBN),又可以威胁攻击型潜艇。举例而言,无人潜航器可以采集敌人潜艇部署区域或航行路线数据,为反潜作战(ASW)提供支持。这样的活动即使在和平时期也会加剧紧张局势,比如2016年12月美国在中国南海东南部水域部署两艘无人潜航器,中国捕获其中一艘,引起中美海军对峙。[23]
更重要的是,发生危机时,一方可以在敌人潜艇基地入口处或海上要道附近部署无人潜航器,追踪尾随潜艇。美国海军无人潜航器发展总体规划明确将“威胁敌方生存”列为无人潜航器的重要任务。[24]无人潜航器对中国弹道导弹核潜艇和攻击型潜艇构成同等威胁,这令中国在危机期间很难判断美国意图。比如,即使美国只想威胁中国的攻击型潜艇而非弹道导弹核潜艇,中国仍有可能怀疑其海上核威慑能力面临危险,这可能使中国做出强烈军事反制措施。而中国的这种强烈反应在美国看来可能又极具挑衅意味,这就可能导致冲突循环升级。事实上,中方的报道暗示,中国2016年12月捕获美国无人潜航器的部分原因,是中国认为在该区域的弹道导弹核潜艇受到威胁。[25]将来一旦发生对峙,如果中国认为其弹道导弹核潜艇受到威胁,中国可能再次采取强硬措施驱逐美国力量,并展开积极行动保卫自己的战略核潜艇。美国可能认为这些行为过于咄咄逼人,从而也采取激烈的反制措施,这可能导致战争升级。
对非核武器及其影响的不同理解
各国对特定武器的理解通常不同,这些分歧通过两种途径对危机稳定性产生重要影响。首先,一方对另一方在危机期间使用某武器的倾向性有不同认知。其次,一方对另一方部署某武器的目的可能存在不同认知,这使得一方无法正确理解对方升级或降低危机的意愿。
对使用倾向性的不同理解
中国自从2007年成功进行反卫星武器试验以来,其对此项技术的兴趣引来国际密切关注。与此同时,中国军事分析人士和评论员曾广泛讨论外太空成为新战场后对国际安全的影响。[26]考虑到太空资产对现代军事行动的重要作用,很多中国分析人士在公开文章和评论中推测反卫星武器将来可能成为显著影响战争结局的战略力量。[27]也有美国官员和分析人士怀疑中国近年开展的一些导弹防御试验其实是伪装的反卫星试验。[28]此情况下,由于反卫星技术和导弹防御技术存在固有共性,加之缺乏公开的试验技术数据,所以很难客观地推导出中国对部署反卫星武器的兴趣有多大,更不必说使用反卫星武器的兴趣。然而,美国官员和分析人士越来越担心将来发生冲突时,中国方面可能使用反卫星武器以剥夺美国在太空的重大利益。
笔者与中国战略界的访谈表明中美专家可能在此问题上存在重要的认知差异。
笔者与中国战略界的访谈表明中美专家可能在此问题上存在重要的认知差异。[29]我们了解到的大部分中国专家严重质疑反卫星武器的真实效果。最常见的观点是中国关于反卫星武器的作用有很多理论探讨,但公开文献中系统性地实际考查反卫星武器显著影响未来战争进程可能性的严肃研究却很少。事实上,多数专家对反卫星武器有助于取得决定性、不对称优势的看法持怀疑态度。这种观点在中国技术专家圈中十分普遍,且与国外学者最近开展的一些研究结果一致:反卫星武器的战场实用性非常有限。[30]相反,支持使用反卫星武器作战的中国专家往往是理论战略家,而较少是军事技术领域专家。
中国战略界的意见不一表明,中国在将来发生军事冲突时,使用反卫星武器的可能性或许没有多数美国官员和专家预测的那么高。这明显有利于危机稳定。但由于美国不完全了解中国对反卫星武器的犹疑情绪,所以不太可能实现本应有的正面效果。发生危机时,美国认为中国很可能较早使用反卫星武器,因此可能将中国反卫星能力的拉动和演练等模糊信号误解为中国可能准备使用反卫星武器,而中国其实并没有。这时,美国可能出现过激反应,对中国反卫星资产和设施启动先发制人的打击,造成不必要的战争或严重升级风险。
各方对造成升级风险的责任人也有不同看法。
此外,各方对造成升级风险的责任人也有不同看法,使得问题更加难以解决。很多中国专家认识到上述升级风险确实存在,但认为这些风险是美国“遇袭即发射”的核政策引起的,因此在降低风险方面,美国应该负主要责任,采取主动措施,比如放弃其“遇袭即发射”的政策。他们认为中国不应因此在采取军事行动时就变得谨小慎微。
对部署目的的不同理解
最近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引发争议,再次证明关于特定技术能力的不同理解会引发升级风险。但这次的情况比中国反卫星武器更为复杂。美国了解中国可能部署反卫星武器的动机,但可能高估了中国使用反卫星武器的意愿。相反,中美对萨德的能力认知不同,对部署目的的看法同样存在分歧,这进一步加大了升级风险和问题解决难度。
2016年7月,美国和韩国方面商定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韩国现有的导弹防御系统仅具备低空防御能力,比如爱国者-2型防空导弹,只能在来袭导弹即将落地前实施拦截。[31]萨德则意在高空拦截中程导弹,多加一层防御。考虑到朝鲜构成的弹道导弹威胁与日俱增,美韩两国为了保护韩国本土目标以及美在韩军事基地,认为部署萨德是必然选择。
中国对萨德及其部署目的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中国主流专家认为萨德最擅拦截射程1000公里(约600英里)以上的弹道导弹,而朝鲜半岛从北到南只有约900公里,朝鲜对韩国构成主要威胁的导弹射程并不到1000公里。因此,很多中国专家得出结论,萨德不能保护韩国不受朝鲜短程导弹威胁,其部署目的直指中国。[32]
另外,中国十分怀疑美国部署萨德只是“用导弹防御系统全面包围中国”战略的一部分,以此破坏中国的战略核威慑力。[33]中国技术专家指出,萨德系统强大的X波段AN/TPY-2雷达,能够监控中国洲际弹道导弹发射弹头和诱饵的过程,也能探测跟踪中国弹道导弹核潜艇从渤海湾发射的弹道导弹,再将采集到的数据传递给美国国土导弹防御系统,大幅提升其对中国洲际核导弹的防御能力。[34]出于以上种种原因,中国专家认为部署萨德严重破坏了中国的核威慑力,给中国带来了战略安全威胁。
美国包括国务院高级官员在内的专家不论在公开还是私下场合,均不认同中国的看法,认为萨德可以有效拦截朝鲜短程导弹,且不会破坏中国核威慑力。美国认为,中国对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有先进的反制措施,如果非要说AN/TPY-2雷达对中国威慑力有影响的话,那也是微乎其微,不会显著破坏中国核威慑力。多数美专家认为中国的担忧没有根据,或者只是出于政治因素而夸大其词。
中美双方的不同看法可能引发升级问题。已经退休的尹卓少将和杨毅海军少将等中国资深军事专家指出,中美一旦爆发军事冲突,中国应当做好攻击萨德的准备。[35]尹卓将军甚至认为将来与美方发生军事冲突时,中国应当先发制人打击萨德。[36]如果中国真的打击萨德系统,中美两方会对中国的意图产生截然不同的理解。
从中国的角度看,美国应当理解中国打击萨德只是为了消除中国核心国家利益——即其核威慑的生存能力——受到的侵犯,使双方战略平衡恢复到萨德部署前的状态。中国会认为自己的打击行为完全可以理解而且十分正当,不应当激起美国的过度反应。相反,美韩决策者不认可萨德对中国构成实际威胁的说法,因而可能认为中方的打击极具进攻性和挑衅性。事实上,由于美韩已经宣布部署萨德的主要目标是应对朝鲜导弹威胁,所以美国和韩国方面甚至可能认为中方打击萨德意在鼓励朝鲜,促使朝鲜对美韩发动更严重的军事挑衅。在这种情况下,美韩和中国对各自利益和冲突背景有截然不同的理解。这些认知分歧会进一步影响美韩的后续反应,以及中国如何解读其反应。
非核技术对风险承担的影响
非核技术影响一国在危机期间承担风险的态度,从而影响到升级态势。如果一国对其应对敌人挑衅的能力有信心,则该国会表现得较能承受风险,可以静候敌人挑衅再发起反击。相反,如果一国对自身应对能力信心不强,则该国会表现得较不愿承担风险,在发生危机时会倾向于在自己尚有回应能力的情况下及早动手。非核技术可以改变一国对其危机应对能力的信心,从而影响该国升级倾向。
非核技术影响一国在危机期间承担风险的态度,从而影响到升级态势。
假如一国知道敌人正在发展的某种能力可以破坏其核威慑力,比如可以打击预警卫星的反卫星武器、或者可以破坏核C3I系统的网络武器,那么在危机期间该国对其核武器生存能力的信心便会下降。于是,该国可能会不愿承担被首先打击的风险,被迫在战争初期尽早使用核武器。
比如,中国专家知道美国政府正研究利用网络武器破坏潜在敌人的战略导弹和核武器的C3I系统,防止敌人在危机期间发射导弹。[37]美国军方对此展开严肃研究的情况也曾被美国媒体进行公开报道。[38]其中一些报道指出,奥巴马政府曾于2014年加强发展针对朝鲜的“主动抑制发射”能力。[39](主动抑制发射指通过网络和电子干扰等方式,先发制人地以动能或非动能方法破坏或阻止敌人正常发射导弹。[40])
美国的高级国防官员曾笼统地对此类工作予以确认。2016年,时任国防部政策副部长的布莱恩·P·麦克科恩(Brian P. McKeon)在国会作证:“我们需要开发大量工具,包括现在正在开发的工具,在发射之前解除威胁,也就是‘主动抑制发射’。发展主动抑制发射能力可以为美国决策者提供更多防御导弹攻击的工具和机会,反过来减轻‘被动防御发射’弹道导弹防御的负担。”[41]在同一场国会作证中,时任美国陆军空间与导弹防御司令部/陆军战略司令部以及综合导弹防御联合功能司令部司令的大卫·L·曼恩(David L. Mann)中将明确承认网络作战属于国防部“全面导弹防御策略”的一部分。[42]中国专家担心美国有对中国实施类似网络攻击的能力。
美国若想发展有效的网络能力,渗透敌人隐秘、复杂而且进行了全面防护的核C3I系统,必须在和平时期不断进行侦查和探测,摸清敌人网络的基本架构,以发现潜在薄弱点和漏洞。[43]而对方可能偶尔会发现美方的这种网络侦查行动,从而开始担心其核威慑可能受到网络攻击。一国对自身弱点的强烈警觉会使其在危机期间更加不愿承担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多种因素可能增加意外升级风险。
首先,即使相对无害的网络入侵也可能使攻击方低估目标国的威胁感知。目标国的核C3I系统可能非常复杂而隐秘。从攻击方的角度看,单单攻入目标国的核C3I系统不一定意味着就能够实施破坏,但目标国可能会高估攻击方的能力和/或意图。如果目标国在危机期间发现其核C3I系统受到敌人网络渗透的蛛丝马迹,它可能无法迅速地了解渗透的确切规模和程度,因而不得不做出最坏的假设。比如,目标国可能担心攻击方已经或正在篡改系统关键数据和/或代码,系统即将遭到致命破坏,而攻击方其实没有此意图或者没有意识到有此能力。目标国由于认为其系统可能即将受到严重破坏,从而感到形势急迫,因此或许会试图在尚未丧失对其核武器的控制能力之前,迅速使用核武器。
其次,目标国可能认为网络攻击是其核力量即将受到动能攻击的前兆。如果一国在危机期间发现其核C3I系统遭到网络渗透,该国可能认为此攻击标志着攻击方已经越过最后红线,正要对其核能力实施先发制人的解除武装打击,而网络渗透也可以用来采集情报帮助进行动能打击。于是,目标国因担心先发制人的动能打击将接踵而至,有可能采取过度反应。之前就有美国学者提出美国可能在发动第一次核打击的同时或者之前首先进行网络攻击,因此假如中美发生军事对峙,中国似乎有正当理由担心美国在发动网络攻击后将随之展开动能打击。[44]
第三,即使一方在危机期间仅仅是得知敌人或许有能力破坏己方的核C3I系统,这也可能会引起误判和反应过度。例如,如果一国发现其核C3I系统受到不明来源的网络攻击,或者碰巧出现技术问题,该国可能误会是对方蓄意发起网络攻击,这可能引发不必要的危机升级。事实上,其他类型的武器也会引起此类风险。比如,若危机期间某预警卫星出现不明问题,不能正常工作,该国如果知道敌人已经在开发或部署反卫星能力,则可能错误地归咎于敌人的蓄意攻击。
第四,无论和平时期还是危机时期,防御网络攻击都会增加意外或未经授权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如果一国认为敌人有能力破坏其发射核武器,则该国会优先确保其发射核武器的命令可以随时被有效执行,而不是预防未经授权发射或错误发射核武器。这两个目标之间是存在一定矛盾的,因此一国必须做出权衡。这种情况下,如果一国感知到严重的敌方网络破坏的威胁,这将促使该国更愿意承受未经授权发射或错误发射核武器的风险,而更重视下令后不能迅速发射核武器的风险。在实际操作中,各国为避免意外或未经授权发射核武器,采用各种程序验证发射命令的可靠性。不过,如果一国担心网络武器干扰验证程序,导致武器不能正常发射,则该国可能会采用较难被干扰、但会增加意外发射风险的其他程序。
中国分析人士已经急切意识到中国核C3I系统可能存在潜在漏洞,尤其是面临网络渗透的风险。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高级军事专家在评论2010年美国沃伦空军基地事故时(当时因技术故障,五十枚洲际弹道导弹失联),指出敌人有可能蓄意攻击国家核指挥控制系统,并强调网络攻击可能造成类似甚至更严重的事故。[45]中国民间学者也强调了中国核指挥控制系统面临的网络威胁。[46]中国很可能已对其核C3I系统实施被动防护措施,比如进行物理隔离以及使用电磁屏蔽技术,[47]不过具体细节尚无公开讨论。此外,即便采用防护措施也不能保证万无一失。正如震网事件所透露的,美国和以色列研发网络武器攻击伊朗纳坦兹的离心设备,即使进行了物理隔离,系统在精密干扰之下仍然十分脆弱。[48]
本章采访的大部分中国专家认为,核C3I系统受到的网络威胁本身并不会增加升级风险,风险是否会增加根本上取决于一国所做的战略选择而非技术问题本身。比如,若一国担心自己的核C3I系统受到网络攻击,那它有两个选择:制定计划在系统被破坏之前使用核武器,或者在发生紧急情况时部署完全不依靠网络的备用C3I系统。如果不考虑备用系统的成本、有效性、可能受其他干扰手段破坏等明显挑战,备用系统也许可以起到稳定危机的作用。中国专家认为,一国应对网络攻击的政策,是一个战略选择影响升级风险的明显例子。由于中国执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所以不会对网络攻击做出核反击。然而,美国政府资助的一些研究则主张不排除对严重的网络攻击启动核报复。[49]
有的中国专家认为,网络技术对危机稳定性有负面影响的流行观点完全基于逻辑推导,没有实际证据,因而对其提出质疑。他们指出,国家在对网络攻击做出启动军事报复的决定时通常会非常小心,网络攻击引起升级的情况非常少见。[50]也有专家认为,一些网络攻击技术具有自我威慑的效果,这使得它们不太可能被轻易使用。他们给出的理由与美国军事战略家成斌(Dean Cheng)的观点类似:“大部分网络武器实际只能使用一次,”一旦使用后,目标就会采取行动修补网络漏洞,使得这种网络武器丧失效用。[51]
最后,少数中国专家甚至指出,网络技术对危机稳定性有积极影响。他们认为,网络技术的发展可以便利各国决策者之间以及决策者与大众之间的沟通。通过先进的网络技术,公众有更多机会了解核对峙升级风险,从而更加不愿承担此类风险,更愿意向国家决策者施压,令其关注有效的危机沟通机制,采取温和措施,缓和军事紧张局势。
技术、战争迷雾与升级
“战争迷雾”一词形容军事领导人不清楚或不完全掌握战场局势,[52]从而会造成误解和误判。本章讨论的许多新兴非核技术有加重或减轻战争迷雾的作用,从而影响升级动态。
一方面,一些中国专家在受访时表示,网络技术可以帮助政府获取、追踪情报。他们认为,先进的网络技术让政府能够高效、详细、及时地监测核武器和核材料的存储和流动,迅速发现异常迹象,有助于改进核武器和核材料的管理,从而降低意外发射核武器或使核材料落入坏人之手的几率。
本章讨论的许多新兴非核技术有加重或减轻战争迷雾的作用,从而影响升级动态。
另一方面,中国分析人士也认识到使用某些非核武器可能妨碍敌人对战场形势的认识。有的中国分析人士(尤其是支持在局部战争中使用反卫星武器打击美国侦查和通信卫星的分析人士)则倾向于认为,反卫星武器能够破坏美国C3I系统的有效性,由此引起的战争迷雾可以为中国带来一定的战术军事优势。[53]
不过,关于降低美国战场形势感知和实时通信能力是否会对中国产生负面影响的讨论甚少。受访中国专家认为,对美国太空C3I资产进行有限打击不会引起核报复,因为这种不成比例的回击是很难想象的。但较少有人注意到另一种可能性,即,由于战争迷雾加重,美国的战场感知能力下降,因此可能将中国军演、调动导弹部队等军事演练行动误解为中国准备使用核武器,因而可能对中国核力量或设施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
中方没有关注到这一种可能性,或许与中国无条件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长期政策有关。由于该政策,中国专家认为,美国同行和他们一样,理应明白中国无意通过首先使用核武器来解决常规军事冲突。因此,他们认为美国不可能把中国其它军事举动误读成即将使用核武器的信号。举例而言,一位中国资深专家认为“中国可能会使用反卫星武器摧毁对方的指挥、控制、通信和情报系统”,但她同时指出“对于中国这样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的国家,反卫星武器显然不会引发核攻击”。[54]这种观点是中国普遍想法的典型,即,不认为错误的认知和理解可能导致核武器的不必要使用,不认为反卫星武器等技术引起的战争迷雾可能影响敌人对形势的正确理解和决策。
浓重的战争迷雾之下可能发生非常危险的事故。比如,若中国反卫星武器攻击美国预警卫星,可能会增加美国对来袭导弹的误报几率。事实上,1995年,俄罗斯陆基预警雷达就把侦测到的挪威探空火箭误认成美国三叉戟潜射弹道导弹。许多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之所以在这次事故中能够及时发现自己的错误,从而没有错误地启动核报复,部分原因是俄罗斯当时拥有一套正常运转的天基预警卫星网络,两套系统相互验证,从而澄清了局势。[55]对于美国和中国的情况,假如美国预警卫星无法运转,其不得不完全依赖陆基和海基雷达探测、核实来袭导弹,那错误警报无法澄清的几率可能会上升。这会增加事件意外升级的可能性,甚至导致错误的核交战。中国分析人士对这些可能性还未进行深入的探讨。
战争迷雾不仅让敌人难以获得准确信息,也阻碍本国与敌国之间信息的有效流动。美国不断加强使用可能破坏中国战略能力的无人军事系统,恰恰说明了此问题。
无人潜航器等无人系统的部署,尤其是在反潜作战中的应用,将带来新的沟通问题,尤其是当一国无人系统与别国的有人系统之间发生冲突之时。有的无人系统完全自动化,无需远程遥控。但远程遥控无人系统与操作员之间的通信连接有可能被切断,甚至有些无人系统本身就不具备向外释放信号的功能。于是,当有人系统和无人系统在海上相遇时,通过相互发信号表明或澄清彼此意图将比当双方都是有人系统时更困难。事实上,新起草的《中美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谅解备忘录》很难直接运用于无人系统。[56]因此,假如远程遥控无人潜航器遇事,操作员可能难以快速辨别原因、准确评估敌人意图。由此引起的不确定性可能增加感知到的威胁,导致意外升级。
更严重的是,中国已经怀疑美国无人潜航器很快就能对中国弹道导弹核潜艇进行实际威胁。因此,危机期间中国一旦探测到美国无人潜航器靠近其弹道导弹核潜艇、或其航线、基地,中国或许不能不假设美国正试图进行战略反潜作战,[57]进而可能提高弹道导弹核潜艇的警戒状态,调动其他力量准备采取强硬行动保护其弹道导弹核潜艇。而如果美国不能充分理解中国的动机,就可能会对此类措施做出过度反应。假如中国发现敌方的有人驾驶核动力攻击潜艇(SSN)威胁到自己的弹道导弹核潜艇,虽然也会引起局势升级,但风险很可能没有无人系统那么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核动力攻击潜艇的指挥员很可能比无人潜航器的操作员经验丰富,也更不愿置自己的潜艇和船员于危险之中,所以会倾向于避免过于挑衅性的行为。此外,正因为核动力攻击潜艇有人操作,中国在采取反制措施应对时,也会比应对无人潜航器更谨慎。
网络和高超音速武器等其他技术可以大大加快战争节奏,缩短决策时间,加剧战争迷雾引起的问题,使升级管理更加复杂化。例如,美国将军曾警告称高超音速武器、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武器会加快未来冲突的节奏,使得未来与俄国和中国的战争变得“极其致命而迅速”。[58]中国专家对网络和高超音速武器的影响持相同观点,并强调此类武器会“显著缩短反应时间”,因此需要开发出更好的情报和信息处理技术。[59]总体而言,中国专家似乎同意西方专家的看法,认为现代战争步伐的不断加快会带来升级风险;但由于他们相信通过开发新能力和制定新的作战程序可以满足不断增长的信息处理和决策速度要求,因此他们对风险管理的前景似乎也更为乐观。
中国专家对网络和高超音速武器的影响持相同观点,并强调此类武器会“显著缩短反应时间”,因此需要开发出更好的情报和信息处理技术。
在新技术背景下,核武器使用决策或面临更紧迫的时间压力。根据对美国“遇袭即发射”政策的相关研究表明,北美防空司令部(NORAD)人员只有约两三分钟时间根据预警系统的评估对来袭情况进行确认。[60]假如使用网络武器破坏北美防空司令部计算机系统,干扰数据通信或数据处理,就会大大增加在规定时间内核实警报真实性的难度。这会导致美国总统无法全面了解形势,可能不得不在信息不全的情况下仓促做出决定。不过,到目前为止中国分析人士还没有深入探讨战争迷雾加重后可能对中国及其敌国的决策、以及升级机制产生怎样的具体影响。
结论
新的先进非核军事技术的发展和部署增加了核能力与非核能力的交缠,可能使升级机制更加复杂而危险。这种影响对中国核领域与战略安全界的多数专家而言仍然属于较新颖的话题。很多专家在文章中表达过担忧,但尚未进行过系统性研究。尽管如此,由于多种原因,中西方学者对此问题的认识仍存在显著分歧。
第一,中国与一些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之间缺乏互信,导致中国处理潜在升级风险、包括意外升级风险的意愿不强。人们普遍认为关于是否、何时以及如何将危机升级或降级的决定直接影响到一国能否实现其战略目标;而中国与美国的竞争关系使中国没有太多兴趣参与讨论升级风险以及共同管理可能的升级风险。中国方面特别担心的是,减轻美国对危机期间潜在升级危险的顾虑可能让美国的行为变得更无所顾忌、更倾向于在其认为适当的情况下升级危机,甚至让中国受到更强的核胁迫。
第二,有中国专家似乎怀疑美国强调升级风险的目的是破坏中国正当的军事现代化工作,尤其是针对可能加剧升级风险的新军事技术的开发。总体而言,发展新军事能力应对西方牵制的迫切需求与考虑升级风险相比更加重要。
第三,中国的传统战略和军事文化也很重要。中国战略家与西方战略家不同,他们历来不强调处理升级问题,尤其是意外升级问题。即便在今天,撰写文章探讨该问题的中国专家依然很少,更不必说去开展深入研究。中国缺乏参与严重核危机的亲身经验,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中国专家不像其美、俄同行那样重视意外核升级的风险。
第四,很多中国专家都认为军事技术本身不会改变升级的风险,反而是具体的部署和运用战略起到决定性作用;也就是说,最终是战略而非技术将决定结果。但另一方面,中国尚未对军事技术的具体部署和运用战略对升级的影响展开系统性研究。
第五,由于中国体制的内部分化,中国核领域与战略界大部分专家只集中于自己的具体专业领域,而深入研究升级问题至少需要三个领域的知识:中国战略武器部署和使用政策;其他国家的战略武器部署和使用政策;以及国际安全战略、军事外交和军备控制问题。体制分化限制了各领域专家之间进行经常性的实质交流,不利于形成研究升级问题所需的全面知识结构。这不仅妨碍中国战略界研究升级风险,也会阻碍中国与国外专家进行深入的实质性讨论。
第六,即使中国和美国都认识到升级风险,但对谁是造成风险和解决风险的主要责任者这一问题仍无法达成一致。比如,假设中国打击美国预警卫星,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认为中国先发制人的反卫星打击策略是意外升级风险的导火索,中国专家却认为美国“遇袭即发射”的政策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于是,双方都认为对方应当负责降低升级风险,而自己无需采取纠正措施。这种思考问题方式无法消除双方关于如何解决升级风险的观点分歧。
尽管存在重重挑战,促进核大国之间就意外升级风险达成共识仍然非常重要。
第七,中国专家担心西方处理升级风险的一些提议——比如将核力量与常规力量分离——可能被潜在敌人利用,方便他们对中国常规力量展开打击。为此,虽然中国部分核力量与非核力量交缠的目的并非为了保护后者,但在认识到交缠可能带来这种好处之后,中国可能不愿将核与非核进行分离而置自己于不利境地。
尽管存在重重挑战,促进核大国之间就意外升级风险达成共识仍然非常重要。升级风险确实存在,且随着交缠的日益普遍而不断增加,但由于中国的相关政策选择,实际风险可能没有很多外国专家所认为的那般严重。
外国专家的担忧很大程度上源于对中国无条件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真诚度或可靠性的怀疑。根据该政策,中国明确并坚定地承诺不会威胁首先使用核武器。从中国的角度看,此政策基本消除了中国方面主动将常规战争升级为核战争的可能性。中国专家对中国核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有着深刻认识,就算不是全部,至少也有大部分专家完全坚信此承诺的可靠性。中国专家大多坚定认为除非绝对确认中国受到了核武器攻击,否则中国绝无意图、也绝不会使用核武器。他们相信,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大大避免了紧张局势和冲突升级的风险。相反,许多国外专家倾向于怀疑中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并不是完全无条件的,因此对中美升级风险的评估较为悲观。
此外,中国高度集中化的指挥控制体系使得中国未经批准或草率使用核力量的可能性低于很多国外分析人士的设想。指挥控制高度集中化是整个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重要特征,包括常规力量和核力量。中国基层军队在作战时的行动自由度通常低于很多西方军队,没有上级明确指示,基层军事指挥官不会过度冒险——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重要文化。因此,危机期间,如果没有接到上级使用核武器的指令,解放军指挥官即使面对己方反击能力被快速削弱的风险,也会避免冒险性行动,不会轻易发射核武器。
中国最高政治领导人掌握着核武器使用权,而且很可能是小范围内的集体决定,而不是个人决定。具体说来,是否使用核武器的最终决策机构可能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甚至是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或者是后者在前者的建议下做出决策)。这样的制度设计使得中国草率发动核战争的几率低于一些国外分析人士的看法。
此外,近年来中国越来越关注意外升级问题。中国官员和专家在与西方各级官员、专家交流过程中,加深了对潜在风险的认识。中美共同制定了海空军事相遇的行为准则和规范。此类规范虽然没有直接涉及核力量、也远谈不上全面,但它们确实说明中国日益重视对军事危机和意外升级风险的处理。它们为两国未来减轻核风险方面的进一步交流和合作铺平了道路。
即便如此,我们在未来仍然面临一些新的挑战。随着西方核思想体系对中国的影响不断加深,有中国专家开始提倡效仿美国的一些核政策。例如,有军事专家认为,中国可以考虑放弃和平时期将其核武器置于低戒备状态的长期做法,而变更为“基于预警发射”。[61]中国目前不断发展的预警系统也为做出类似政策转变提供了技术基础。[62]
美国不断投资开发新军事技术,比如可以干扰核C3I系统的网络武器、可以威胁敌人弹道导弹核潜艇的无人潜航器以及可以引起各种不确定性的高超音速武器,也会鼓励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紧随其后进行同类技术竞争。如此模仿会加剧交缠现象,导致将来升级管理进一步复杂化。
为了应对交缠和意外升级挑战,中美必须加强战略互信。
为了应对交缠和意外升级挑战,中美必须加强战略互信。目前的信任缺乏直接导致中国怀疑美国的战略意图,无心与美国专家就相关问题进行交流。即便如此,通过交流处理升级风险和增强互信其实是相辅相承的。国外专家与中国专家之间的持续性对话,可以让双方均有机会深入、全面了解彼此的真实认知和关切。长期看来,这样的过程有助于双方逐渐减少直至消除对彼此意图的疑虑,建立互信,形成良性的互动循环。
建立信任措施可以促进深入合作,处理交缠产生的升级风险。如果美国方面向中国领导人明确承认双边核能力相互脆弱性的基本事实、且美国愿意在此基础上制定战略力量发展和部署方案,将非常有助于建立互信。这一政治承诺虽然不能进行绝对的验证,但依然会起到降低中国担心美国方面意图利用非核手段对付中国的小型核武库的作用,这会提高中国与美国讨论交缠问题、进而合作处理升级风险的意愿。中国也可以进一步阐明其对一些引起交缠并引发美方关切的技术认知。例如,中国可以就未来高超音速武器是安装常规弹头还是核弹头,以及哪些太空资产在哪些情况下可以成为正当攻击目标与美国展开讨论。
这些透明度措施不会涉及敏感军事信息,也不会破坏国家安全,而是有助于促进双方开展实质性探讨,澄清并减少非理性的威胁观,降低危机期间过度反应的可能性。考虑到中美降低意外升级风险的共同利益,这样的对话有望带来深入交流,带来在先进非核技术时代降低风险的单边和合作措施。
注释
[1] 本节部分研究基于:赵通《中美建立相互信任的核关系:交战影响》(博士论文,佐治亚理工学院,2014),https://smartech.gatech.edu/handle/1853/53021.
[2] 毛泽东《毛泽东军事文选》(北京:人民解放军出版社,1981).
[3] 王缉思和徐辉《中美危机行为比较分析》,载于2005年《美国研究》第2号.
[4] 雨驿《由珍宝岛引发的中苏核战危机》,载于2009年 《党员干部之友》第12号;陈昊《周恩来在珍宝岛事件前后》,载于2010年《党史博采纪实》第1号;威廉·伯尔(William Burr)《1969年美苏关系:中苏边界战争与和解之路》,载于2001年《冷战史》卷1第3号.
[5] 戴维斯·B·博布罗(Davis B. Bobrow)、史蒂夫·陈(Steve Chan)和约翰·A·克林根(John A. Kringen)《理解外交政策决定:中国案例》(纽约:纽约自由出版社,1979).
[6] 张沱生《张沱生谈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全球性大国要拼危机管控》,载于2013年《国家人文历史》第24号.
[7] 迈克尔·D·斯韦因(Michael D. Swaine)、张沱生和丹尼尔·F·S·科恩(Danielle F. S. Cohen)《管理中美危机:案例研究与分析》(华盛顿特区: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2006).
[8] 乔夫里·福尔登(Geoffrey Forden)《中国如何输掉即将到来的太空战争》,载于2008年1月1日《连线》,https://www.wired.com/2008/01/inside-the-chin/.
[9] 国防部长办公室《2016年呈国会年度报告: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和安全发展》,国防部,2016.
[10] 迈卡·赞寇(Micah Zenko)《危险的太空事件》,外交关系协会应急计划备忘录第21号,2014年4月16日,https://www.cfr.org/report/dangerous-space-incidents.
[11] 芭芭拉·奥帕尔-罗马(Barbara Opall-Rome)《美国希望与中国设立类似美俄热线的太空碎片处理热线》,载于2012年2月13日太空新闻网,http://spacenews.com/us-wants-space-debris-hotline-china-patterned-one-russia-0/.
[12] 作者对中国核问题专家的访谈,北京,2016年7月.
[13] 约翰·威尔逊·刘易斯(John Wilson Lewis)和薛理泰《假想敌:中国为不确定的战争做准备》(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6).
[14] 大卫·克罗默·洛根(David Cromer Logan)《划分中国常规武器和核武器》,载于2015年5月5日《原子科学家公报》,http://thebulletin.org/drawing-line-between-conventional-and-nuclear-weapons-china8304.
[15] 郭达安(Michael Glosny)、杜孟新(Christopher Twomey)和瑞恩·雅各布斯(Ryan Jacobs)《中美战略对话第八阶段报告》,海军研究生院,2014年8月.
[16] 福尔登(Forden)《中国如何输掉即将到来的太空战争》;山姆·塞茨(Sam Seitz)《太空武器化和反卫星威胁动态》,载于2016年7月14日全球情报信托,http://www.globalintelligencetrust.com/sam-seitz/dynamics-of-space-weaponization-and-the-asat-threat;和奥帕尔-罗马(Opall-Rome)《美国希望设立太空碎片处理热线》.
[17] 菲奥娜·S·坎宁安(Fiona S. Cunningham)和M·泰勒·弗拉韦尔(M. Taylor Fravel)《确保保证报复:中国核态势与中美战略稳定,”《国际安全》40,第2号(2015):45.
[18] 李彬等人,“中国为什么要进行核武库现代化,” 卡内基国际核政策会议,华盛顿特区,2015年3月24日,http://carnegieendowment.org/2015/03/24/why-is-china-modernizing-its-nuclear-arsenal-pub-57516.
[19] 王长勤和方光明《我们为什么要发展东风-26弹道导弹》,载于2015年11月23日《中国青年报》.
[20] 詹姆斯·M·阿克顿(James M. Acto)《高招?提出关于全球快速常规打击的正确问题》(华盛顿特区: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2013).
[21] 夏立平《‘高边疆’ 理论视阈下美国全球快速常规打击计划》2014年《国际观察》第5号;姚云竹《中国不会改变核政策》,载于2013年4月22日中美聚焦网,http://www.chinausfocus.com/peace-security/china-will-not-change-its-no-first-use-policy.
[22] 唐纳德·H·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H. Rumsfeld)《核态势评估报告:序言》(华盛顿特区:国防部,2002),http://archive.defense.gov/news/Jan2002/d20020109npr.pdf.
[23] 芭芭拉·斯塔尔(Barbara Starr)和瑞恩·布朗(Ryan Browne)《五角大楼要求中国归还美国无人潜航器》,CNN 2016年12月17日报道,http://edition.cnn.com/2016/12/16/politics/chinese-warship-underwater-drone-stolen/.
[24] 美国海军部《美国无人潜航器(UUV)总体规划》,2004年11月9日,http://www.navy.mil/navydata/technology/uuvmp.pdf.
[25] 子默《中美南海暗战升级 潜航器牵出核潜艇》,载于2016年12月17日多维新闻.
[26] 戴旭《太空战幽灵逼近》,载于2010年党政干部参考第8号.
[27] 赵楚《太空战:挑战、重点与对策—本刊召集解放军专家研讨太空战趋势与对策》,载于2001年《国际展望》第9号.
[28] 迈克·格鲁斯(Mike Gruss)《美国国务院:中国反卫星武器试验》,太空新闻网2014年7月28日报道,http://spacenews.com/41413us-state-department-china-tested-anti-satellite-weapon/;比尔·戈尔茨(Bill Gertz)《中国反卫星武器试验》,华盛顿自由灯塔报2015年11月5日报道,http://freebeacon.com/national-security/china-tests-anti-satellite-missile/.
[29] 作者北京访谈,2016年6月-7月.
[30] 贾格纳许·桑卡兰(Jaganath Sankaran)《中国对美国反卫星威胁的局限性》,载于2014年《战略研究》第19号.
[31] 美韩现正将韩国的爱国者-2改进型防空导弹系统升级为爱国者-3改进型防空导弹系统。
[32] 樊高月《韩国部署“萨德”弊大于利》,载于2016年4月13日中美聚焦,http://cn.chinausfocus.com/peace-security/20160413/4811.html.
[33] 《克林顿表示美国可以‘用导弹防御系统包围中国’》,载于2016年10月14日芝加哥论坛报,http://www.chicagotribune.com/news/nationworld/politics/ct-hillary-clinton-china-20161014-story.html;何兴强《美日搭建导弹防御系统剑指何方》,载于2007年7月10日《中国国防报》.
[34] 吴日强《美国要在韩国部署‘萨德’,对中国国家安全会有哪些影响?》,腾讯讲武堂,2014,http://www.globalview.cn/html/military/info_9055.html;李彬(音,Li Bin)《韩国安全难题与萨德部署》,载于2016年8月3日《京乡新闻》.
[35] 翟亚菲(Di Yafei)《六位大使将军激辩‘萨德’:韩国是不是中国的‘敌人’?》,载于2016年7月14日《环球时报》,http://mil.huanqiu.com/observation/2016-08/9331382.html.
[36] 吴攸(Wu You)《解放军:若开战第一时间打掉萨德基地》,载于2016年7月11日多维新闻,http://global.dwnews.com/news/2016-07-11/59752736.html.
[37] 方勇《2015 年世界武器装备与军事技术发展重大动向》,载于2015年《军事文摘》第23号;邓思家(Deng Sijia)《美研发反导新技术:无人机发射激光 敌发射前打击》,载于2016年10月28日《解放军报》.
[38] 比尔·戈尔茨(Bill Gertz)《五角大楼开发导弹发射前网络攻击技术》,载于2016年4月14日《华盛顿自由灯塔报》,http://freebeacon.com/national-security/pentagon-developing-pre-launch-cyber-attacks-missiles/;小悉尼·J·弗里德伯格(Sydney J. Freedberg Jr.)《联合参谋部研究导弹防御新方案》,载于2015年9月16日《打破防御》,http://breakingdefense.com/2015/09/joint-staff-studies-new-options-for-missile-defense/.
[39] 大卫·E·桑格(David E. Sanger)和威廉·J·布罗德(William J. Broad)《特朗普继续对朝鲜导弹的秘密网络战》,载于2017年3月4日《纽约时报》,https://www.nytimes.com/2017/03/04/world/asia/north-korea-missile-program-sabotage.html.
[40] 里基·埃里森(Riki Ellison)《主动抑制发射》,导弹防御支持联盟,2015年3月16日,http://missiledefenseadvocacy.org/alert/3132/.
[41] 弹道导弹防御政策与项目: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战略部队小组委员会听证会,第114次会议(国防部政策副部长布莱恩·P·麦克科恩(Brian P. McKeon)声明,2016年4月13日),https://www.armed-services.senate.gov/imo/media/doc/McKeon_04-13-16.pdf.
[42] 弹道导弹防御政策与项目: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战略部队小组委员会听证会,第114次会议(美国陆军空间与导弹防御司令部/陆军战略司令部以及综合导弹防御联合功能司令部总司令大卫·L·曼恩(David L. Mann)中将声明,2016年4月13日),https://www.armed-services.senate.gov/imo/media/doc/Mann_04-13-16.pdf.
[43] 《关键基础设施主动网络防御》,载于2013年《土耳其国防》8卷第48号.
[44] 斯蒂芬·J·辛巴拉(Stephen J. Cimbala)《中国军事现代化:控制战略核武器的影响》,载于2015年《战略研究季刊》9卷夏季第2号,http://www.airuniversity.af.mil/Portals/10/SSQ/documents/Volume-09_Issue-2/cimbala.pdf.
[45] 《美国50枚核弹失控 世界惊魂一小时》,CNTV 2010年11月1日报道,http://tv.cntv.cn/video/C11237/d31e43c4849c4d92131a64a653619561.
[46] 程群和何奇松《构建中国网络威慑战略》,载于2015年《中国信息安全》第11号.
[47] 刘学观等人《电磁脉冲弹及其防护》,载于2003年《通信技术》第9号.
[48] 金·泽特(Kim Zetter)《黑客词典:什么是气隙?》,载于2014年12月8日《连线》,https://www.wired.com/2014/12/hacker-lexicon-air-gap/.
[49] 里查德·A·克拉克(Richard A. Clarke)和斯蒂夫·安德瑞森(Steve Andreasen)《网络战威胁不应当成为制定核威慑新政策的理由》,载于2013年6月14日《核威胁倡议》,http://www.nti.org/analysis/opinions/cyberwars-threat-does-not-justify-new-policy-nuclear-deterrence/.
[50] 刘杨钺《网络空间国际冲突与战略稳定性》,载于2016年《外交评论》第4号.
[51] 成斌,“太空和网络威慑前景:中国案例,”传统基金会,2016年1月21日,http://www.heritage.org/defense/report/prospects-extended-deterrence-space-and-cyber-the-case-the-prc.
[52]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论战争》迈克尔·霍华德(Michael Howard)和皮特·巴瑞特(Peter Paret)编译(新泽西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6);《越战烟云: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的宝贵十一课》埃罗尔·莫里斯(Errol Morris)执导(2003年纽约州纽约市;索尼经典影片);威廉·A·欧文斯(William A. Owens)和艾德·欧弗利(Ed Offley)《拨开战争的迷雾》(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2001).
[53] 李大陆《论 “不对称” 军事制衡》,载于2015年《太平洋学报》第5号;李丹、焦彦平、高小玲和王敏《反卫星武器及其防御措施研究综述》,载于2009年《测控技术》第28号.
[54] 吴莼思《反卫星烟幕》,载于2015年5月28日《原子科学家公报》,http://thebulletin.org/space-weapons-and-risk-nuclear-exchanges/antisatellite-smoke-screen。
[55] 福尔登(Forden)《中国如何输掉即将到来的太空战争》;乔夫里·福尔登(Geoffrey Forden)、帕维尔·波多维格(Pavel Podvig)和西奥多·A·波斯托尔(Theodore A. Postol)《错误警报与核危险》,载于2000年《IEEE综览》37卷第3号。
[56] 美国国防部与中国国防部《美利坚合众国国防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关于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的谅解备忘录》,2014年11月9日-10日,http://archive.defense.gov/pubs/141112_MemorandumOfUnderstandingRegardingRules.pdf.
[57] 刘畅《美军无人潜航器对中国有何危害?》,载于2016年12月19日《凤凰军评》;张强《无人潜航器到底是个什么‘神器’》,载于2016年12月17日《科技日报》.
[58] 塞缪尔·奥斯本(Samuel Osborne)《美国将军警告将来与俄罗斯和中国的战争“极其致命而迅速”》,载于2016年10月6日《独立报》,http://www.independent.co.uk/news/world/future-war-russia-china-us-extremely-lethal-fast-artificial-intelligence-cyber-warfare-a7347591.html.
[59] 严国群和陶中华《世界新兵器:高超音速武器发展引人注目》,载于2003年2月19日《解放军报》;陈光文《高超音速武器成大国新竞技场》,载于2016年3月29日《国际先驱导报》.
[60] 《“攻击下即发射反击”是否可行?》,载于2016年8月4日核威胁倡议网站.
[61] 寿晓松《战略学》(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3).
[62] 赵通《战略警告与中国核态势》,载于2015年5月28日《外交官》,http://thediplomat.com/2015/05/strategic-warning-and-chinas-nuclear-posture/.
关于作者
赵 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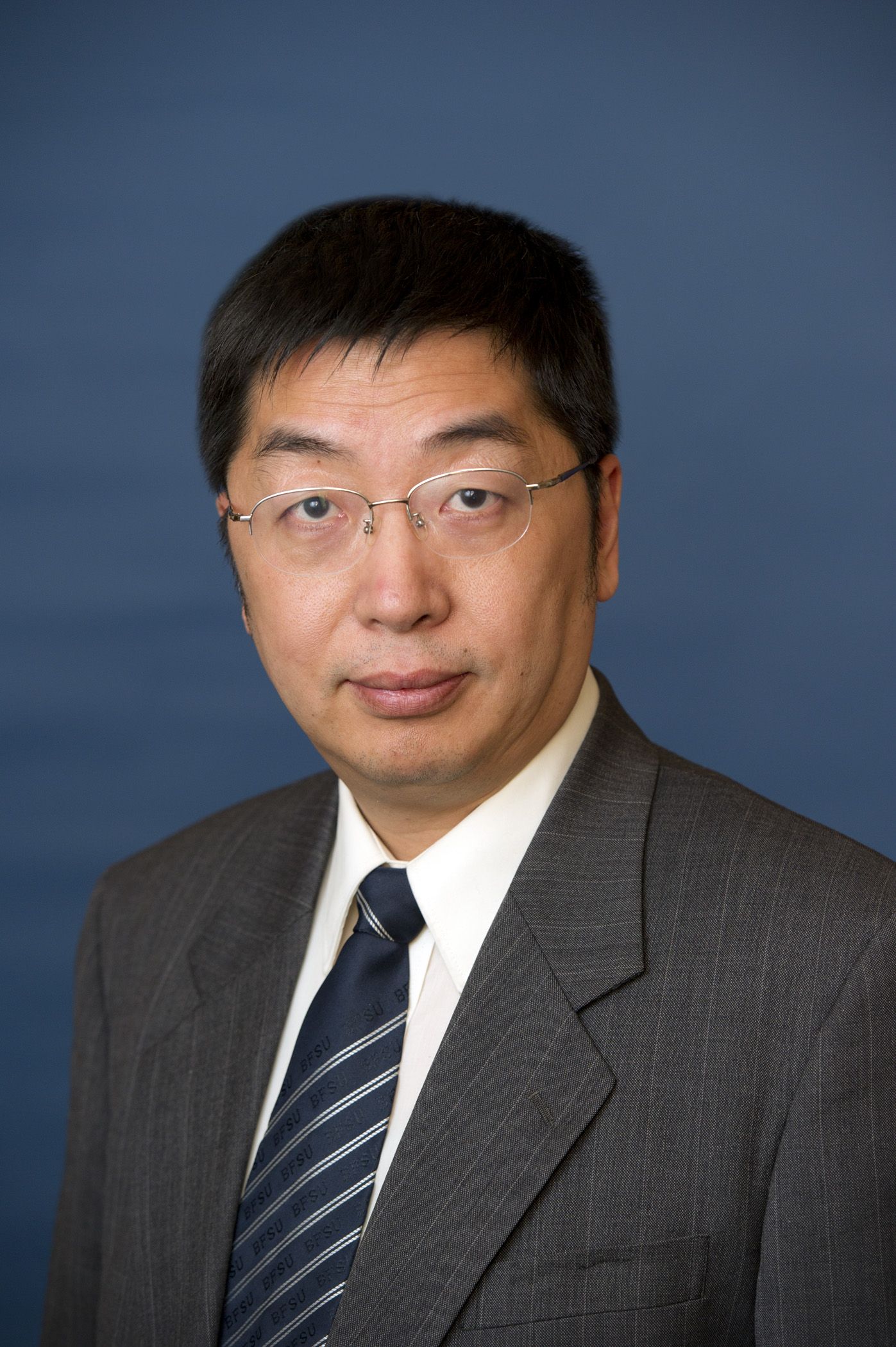
前资深研究员, 亚洲项目、核政策项目
作为核裁军领域的专家和物理学家,李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的核政策、军备控制政策以及中美核关系等方面。
非核武器与核力量及其支持力量日益交缠,若试图降低由此而产生的意外升级风险,首先必须对所涉及的风险建立深刻的理解。由于风险取决于认知因素——冲突一方对敌对方意图的认知,因此重要的是,美国方面应理解俄国方面和中国方面的关切,同时俄方和中方也需理解美方的关切,无论这样的关切看起来是否公平、合理。
在此背景下,前几章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是:中俄传统和当代战略思想几乎没有关注到意外升级的可能性。中俄专家对意外升级并未表示出严重的担忧,本卷的中国作者亦是如此(不过赵通和李彬强调,他们比许多西方专家都更为乐观)。中俄最普遍的假设是冲突期间发生的任何暴力升级都是蓄意的。比如,阿列克谢·阿尔巴托夫(Alexey Arbatov)、弗拉基米尔·德沃尔金(Vladimir Dvorkin)和彼德·托皮契卡诺夫(Petr Topychkanov)表示:“当代俄国战略家会出于本能地假设,使用武力(包括核武器)的决定都是理智的”。类似地,赵通和李彬指出:
中国长期以来相信最高决策者可以较充分地掌控战争的具体进程,从而没有过多考虑战争进程可能涉及的诸多不确定因素,尤其是最高决策者可能并不能完全实时了解战场态势、或者不能有效管控具体军事行动的风险。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越是认为意外升级不可能发生,反而越会增加此类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持有该观点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在和平时期不太会采取措施降低风险,但在战争时期却会按最糟糕的情况解读模糊事件。
俄国和中国方面都假定美国会试图使用先进的常规力量破坏中俄的核威慑。因此,美国的非核行动若意外涉及中俄任意一国的核力量,便存在被解读为故意使用常规力量打击对方战略军事目标的风险,令人担忧的是,大规模常规冲突期间美国常常需要付诸此类常规打击行动。比如,阿尔巴托夫、德沃尔金和托皮契卡诺夫指出:“原本针对俄国一般性海军舰艇和飞机展开的打击,也可能无意中摧毁同一基地的战略潜艇和轰炸机。”
对两用支持力量尤其是预警卫星的非核打击,可能造成更严重的升级风险。就这一点而言,双方作者意外达成共识:不仅是美国对中国或俄国的打击会引发升级,中国或俄国对美国的打击也会如此。
举例而言,赵通和李彬指出,中国战略界部分专家呼吁在美中发生冲突时打击美国的预警卫星,“削弱美国战区导弹防御能力,从而确保中国常规导弹可以有效打击美国和/或台湾目标”。他们进一步提出:
虽然一些中国专家明白美国的预警卫星也为核大战提供战略预警,但他们似乎认为美国肯定能够正确理解中国在常规、有限、局部战争中使用反卫星武器的意图。他们的理由是中国并没有能力威胁美国的大规模核力量,所以美国应该明白中国即使破坏了美国战略预警能力也无法借此对美国进行先发制人的核打击而不遭受核报复,所以破坏美国的战略核能力不可能是中方使用反卫星武器的意图。但在很多美方专家眼里,中国可能对美国小规模地首先使用核武器,以便对美国进行恐吓、而非试图先发制人地解除美国的核武装;因此,美国认为中国攻击美国预警卫星确实有可能是对美使用核武器的先兆。
即便如此,中俄双方分析的重点是源自美国的升级风险。在此背景下,双方作者认为,各种科技的进步,特别是高超音速助推滑翔武器的研发,会让问题发酵。赵通和李彬指出,中国专家“一直认为美国有意使用高超音速武器对中国的核力量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因此中国政府“可能将某些来袭的高超音速武器解读为旨在打击中国的核力量”(与弹道导弹不同,助推滑翔武器具有机动性,打击之前无法确定其目标。如果美国向中国既有核力量又有非核力量的某地发射助推滑翔武器,将会造成不确定性。)
与此同时,阿尔巴托夫、德沃尔金和托皮契卡诺夫则关注来袭助推滑翔武器的探测挑战。俄国高度依赖“遇袭即发射”政策,以此加强其洲际弹道导弹(ICBM)的生存能力,所以早期探测对俄国而言至关重要。阿尔巴托夫、德沃尔金和托皮契卡诺夫指出:
地面雷达只能探测到即将落地的来袭滑翔武器,而这时若想发射洲际弹道导弹为时已晚。因此,只能在卫星探测到助推滑翔武器发射信号时,就实施“遇袭即发射”方案,而无需地面雷达确认。
毋庸置疑,俄国以单一探测技术为依据发射洲际弹道导弹的政策并不值得推崇。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也可能迫于压力而采用类似政策。赵通和李彬指出,中国国内有声音呼吁考虑采取“基于预警发射”战略,且中国正在研究相应技术。若中国真的转变其战略,那么其同样会面临俄国制定计划应对美国助推滑翔攻击时所遭遇的挑战。
即便如此,俄国和中国目前的核力量态势迥然不同,两国可能对美国发起的常规战争的特征也存在显著差异。因此,美俄冲突的升级动态可能与美中冲突有重大区别。理解每种形势的特点非常重要。
俄国当代战略思想的核心是对抗美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空天战争概念。正如阿尔巴托夫、德沃尔金和托皮契卡诺夫指出的,空天战争的含义难以捉摸,是“涉及核作战和非核作战、防御能力和进攻能力、弹道武器和飞航武器等科技与作战连续且统一的持久状态。”他们表示这样的冲突将成为“交缠的温床”。
俄国核态势进一步推动着交缠。俄国拥有大批战术核武器,可能在冲突早期便投入使用。阿尔巴托夫、德沃尔金和托皮契卡诺夫估计,俄战术核武器“运载工具与常规力量和武器共用基地,也可以结合常规力量和武器使用……所以可能会遭到攻击”。更令人担忧的是,交缠可能导致俄国“为击败参与常规冲突、开展常规军事打击的美国海军和空军”,而“对机场、海军基地及其C3I[指挥、控制、通信和信息]设施展开有限战略打击”。需要强调的是,有限战略打击并不属于俄国官方的公开政策,但政府所属专家却公开对此表示支持,西方分析人士(或者至少未获得机密信息的西方分析人士)似乎尚未开展过此类讨论。
中国的核力量比俄国规模小、种类少,且中国声称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此立场虽然能降低一些交缠风险,但同时也会加剧另一些风险。例如,由于中国核力量比俄国要小得多,中国政府可能更担心常规军事力量打击的可能性,虽然中国也不太可能使用核武器攻击其认为威胁到其核威慑的美国非核力量。赵通和李彬重点指出,由于美国和中国互不信任,所以不太可能实现中国核政策本应取得的效果。需特别注意的是,中国专家普遍对中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有着“坚定信念”。因此,他们往往认为,美国不会将中国打击预警卫星等模糊行动理解为中国准备使用核武器。李彬和赵通也指出,许多国外专家“质疑中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并不是完全无条件的”,因此实际发生误解的程度显然要大得多。
战区的战略地理位置也会影响将来可能出现的冲突升级风险。海军作战是除欧洲地面战争之外的重要战争,也是美中冲突的核心。[1]在此背景下,美国无人潜航器(UUV)和中国近来部署的弹道导弹核潜艇(SSBN)可能发生危险互动。赵通和李彬指出,中国担心在不远的将来,美国“可以在敌人潜艇基地入口处或海上要道附近部署无人潜航器,追踪并尾随敌方潜艇”。这不仅威胁到中国弹道导弹潜艇和攻击型潜艇,而且“即使美国只想威胁中国的攻击型潜艇而非弹道导弹潜艇,中国仍有可能怀疑其海上核威慑能力面临危险,这样的风险确实存在”。而这样的交缠不是无人潜航器独有,美国攻击型潜艇也能威胁到中国弹道导弹潜艇和攻击型潜艇。不过,无人潜航器所引发的问题更复杂,无人潜航器的部署数量可以远超攻击型潜艇,而且无需部署船员,承担的任务也比攻击型潜艇更具攻击性且风险更高。
俄国和中国对核系统和两用C3I系统可能遭到网络攻击的担忧存在重要差异,但其原因复杂。赵通和李彬认为,“中国分析人士已经急切意识到中国核C3I系统可能存在潜在漏洞,尤其是面临网络渗透的风险”。他们认为,中国在这样的认识之下,一旦核C3I网络遭到渗透,即使攻击方的目的只是从事间谍活动,升级的风险也会很高。相反,阿尔巴托夫、德沃尔金和托皮契卡诺夫则不太担心网络武器的升级影响(不过他们也指出由于该领域的机密性,甚至不可能得出“稍微具体的”结论)。特别是,他们认为,虽然一国核C3I系统的预警卫星等组成部分易受网络干扰,但与战略核力量直接通信的系统是“独立且受高度保护的”,因此“很可能不会受到网络攻击”。俄国缺乏这方面的文献研究,若以此为依据,则可以说俄国的分析界普遍都持此观点。当然,要想评估升级风险,最关键的还要看俄国政府和军方的观点,而他们的观点是否与非政府分析人士一致则不得而知。
处理升级风险最实际的方案是实施单边措施,至少最初阶段应该如此。有的单边措施不可避免地需要采取保密方式进行,如修订战争计划等,这会导致外界难以衡量其进度,但仍然会非常有效。毕竟,交缠引起的升级风险主要取决于一国拥有的武器系统,其如何在和平时期部署、在战争时期使用武器,以及其政治和军事领导人理解这种行动可能让敌人产生的认知及其对正确理解敌人行动所存在的挑战的认识。危机期间加强战略决策负责人对意外升级风险的意识、并在制定政策和规划战争时考虑到此风险,对于降低风险具有很大助益。需要清楚的是,将升级风险纳入政策和规划考虑中,并不意味着它们永远优先于其它作战考虑因素,而是意味着在评估新武器系统或作战理念是否符合一国利益时,应当在决策流程中对该因素给与足够的重视。
理想情况下,美中俄三国都应当按此流程操作,无论其他两国有何举动。当然,考虑到中俄认为意外升级的可能性不大,中国或俄国方面是否会采取行动非常值得怀疑,而本届美国政府是否会对此投入时间或精力也不容乐观。不过,三国政府应当都知道单边秘密措施不会让他们损失什么,反而可能会有很大收益。三国非政府分析人士可以发挥一定作用,让所在国家政府酌情公开或私下强调升级风险的潜在严重性。
在采取这些内部措施的期间也可以同时展开第二步,即,开始政府间的讨论。政府间讨论的主要目的很简单:深入了解潜在对手的观点,更准确地评估升级风险。考虑到环境对于决定升级风险的重要性,可以不进行三边对话,而是分别进行美中和美俄对话。
使各方感到对话确实能加强彼此了解的互惠感,是持续对话的关键。在此背景下,赵通和李彬提出了一些中美之间可以增进互信的具体领域。他们认为如果美国方面“向中国领导人明确承认双边核能力相互脆弱性的基本事实、且美国愿意在此基础上制定战略力量发展和部署方案”,则中国可以考虑“就未来高超音速武器是安装常规弹头还是核弹头,以及哪些太空资产在哪些情况下可以成为正当攻击目标与美国展开讨论”。阿尔巴托夫、德沃尔金和托皮契卡诺夫的工作表明,美俄就这两个问题——先进常规武器和太空核C3I资产的生存能力——展开对话也可以取得丰硕成果。美中、美俄讨论的第三个潜在重点是网络武器与核C3I系统的相互作用。对于俄国而言,可以从最基本的问题开始讨论,即俄国是否觉得这类问题有讨论的价值。
美国和俄国商定讨论战略稳定性,期间可能会涉及交缠的升级后果。虽然第一轮对话已于2017年9月进行,但很难乐观期待该对话取得实质性成果。美中对话则更难启动,李彬和赵通已经解释了其原因。期间,非官方参与者的第二轨道讨论有助于弥补认知差异,也有望为政府间的对话铺平道路。
长期看来,树立合作信心甚正式控制军备对于降低风险都有重要作用,但眼下实施此类措施的前景黯淡(达成这些措施的前提条件就是政府间展开讨论,而目前看来政府间讨论可能遥遥无期)。尽管如此,政府可以也应当启动制定和评估提案的工作。
阿尔巴托夫、德沃尔金和托皮契卡诺夫对美俄关系提出了三个具体建议:制定透明度协议,阻止向对方“战略目标”范围发射巡航导弹的空射和潜艇平台“秘密集结”;协商禁止测试、部署专用反卫星武器;同时洲际助推滑翔系统不得超过《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后续条约规定的限度。美国和俄国应当评估是否可以接受以上建议,如若不能,则评估是否可以修改到可接受的程度。比如,美国方面长期以来一直担忧禁止使用反卫星武器根本无法核实。不过,重点讨论旨在保护同步轨道或高椭圆轨道卫星(属于核心太空核C3I资产)的建立信任措施可能更容易实现。美国和俄国应当自行考量哪些建立信任理念的互利性已达到可单独进行谈判的程度,而哪些只能通过更广泛的一揽子方案讨论。同样,如果政府没有行动,则非政府分析人士可以着手探讨以上问题。
采取措施面临的挑战有的很明显,有的则不然。赵通和李彬提出了经常被忽视但可能很严重的一个挑战:责任问题。他们指出,很多中国专家认为引起升级风险的是美国,因此应当由美国方面采取纠正措施。同样,有美国官员认为,中国选择使用某些C3I能力同时支持核行动和非核行动,中国也应当对该政策的后果负责。美国和俄国互相谴责的场景也不难想象。
然而,谴责在核时代没有实际意义。考虑到各国共同面临着意外升级风险,管理风险的责任也应由多国共同承担。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美国和苏联经历巨大危险方才达成共识,开始降低风险的停止/启动流程。而遗憾的是,美俄领导人似乎忘记了当年的教训。此外,由于中国涉身严重核危机的经历十分有限,中国领导人尚未对此类教训有深刻感受。无论美俄、美中存在怎样严重的分歧,没有哪个国家希望其降低意外升级风险的努力在出现了严重的核战争风险之后才起作用。
注释
[1] 由于各种原因,由无人潜航器引起的升级风险,至少从直觉上讲似乎在美中冲突中比在美俄冲突中严重得多。俄罗斯弹道导弹潜艇力量规模大于中国,遍布两大洋,而且似乎比中国更低调。另外,西太平洋的海军要塞一般比北大西洋更隐密。不过,验证此直觉是否正确还需要很多研究。需特别注意的是,白海(俄罗斯北方舰队基地所在处)与巴伦支海之间有一条非常狭窄的航道,美国无人潜航器可能对该地产生的影响尤其值得关注。
关于作者

联席主任, 核政策项目
詹姆斯•阿克顿(James M. Acton)主要研究核威慑、裁军、不扩散以及核能等问题。
- 交缠导致升级:指挥控制系统的脆弱性将如何增加非故意核战争的风险媒体报道
阿克顿 詹姆斯•
最新作品
更多作品来自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 家庭消费增长对中国GDP增长的影响评论
如果未来五到十年,中国的平均消费增长率确实保持在3-4%之间,那么这必然也是中国GDP增长的上限。
迈克尔• 佩蒂斯
- 中国对全球南方政策背后的挑战评论
尽管中国将保持作为全球南方国家中一个重要的政治和经济力量,但其通过全球南方来制衡美国和全球北方的雄心计划远非十拿九稳。
龚 雪
- 向北京倾斜?李强访马后的马中关系评论
马来西亚的行动表明,该国将继续奉行包容和审慎的“等距”外交政策。
郭 清水
- 新领导人,新的对华路径?评论
过去三年来,东南亚多国领导人发生了重要更迭。这些新领导人将采取怎样的对华路径,与前任领导人有何不同?
- +4
查曼· 米萨卢查· 威洛比, 郭 清水, Lak Chansok, …
- 中国的资金如何影响太平洋评论
为什么尽管太平洋岛国对于持续的债务问题存在担忧,却依然愿意同中国开展合作?
达莎娜· 巴鲁阿, 萨蒂延德拉• 普拉萨德, 张 登华












